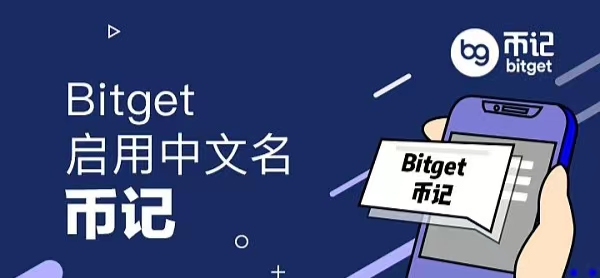我八岁那年在电视上看了一部叫做《森林大帝》的动画片,它讲述了一只小狮子在爸爸被偷猎者射杀后,经历重重磨难最终成长为狮子王的故事。从那以后,我开始了解并喜欢上了狮子,几乎每周都会做关于它们和非洲的梦,有时候甚至会梦到自己去到非洲和狮子共同生活。这个梦想一直伴随着我成长,但它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在1980年代的中国,出国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人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圆梦。

19岁的我在大学时选择了英语作为主修专业,因为我知道英语在非洲的运用非常广泛。大二那年我又把法语选作第二外语,因为法语也是非洲的常用语言。《人猿泰山》给了我写学术论文的灵感,于是我把论文主题定为“回归自然”。这样的题目和其他同学的相比,显得奇怪而又出格,但我深知自己的内心感受:我听到的是来自非洲的呼唤。
图书馆和书店是我高中以及大学时代最爱去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机会阅读到各种各样关于非洲和狮子的书籍。1996年大学毕业后,我去到重庆,并顺利找到了一份还算可靠的公务员工作,随后,我在这座山水之城连续工作了15年之久,但心中对非洲的向往还是一如既往的强烈。作为一个负责国际友好城市项目的政府工作人员,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到国外。那时候我的足迹遍布了全球60个国家,却一直没能去到非洲。我变得愈发焦躁,直到2004年终于等来了机会——31岁的我也终于如愿以偿。虽然我和几个朋友只在非洲呆了短短四天,但在这期间我们在马赛马拉见到了狮子!那是我人生中一次真正与野生狮子碰面的经历!我的梦想真的实现了!

我们在一棵无花果树的旁边与一整个狮群相遇:一头公狮、四头母狮和七只幼狮。它们离我是那么的近,甚至让我有了和家人呆在一起的感觉!那一刻我已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还在做梦。我们在这里停留了大约20分钟,直到朋友们纷纷催我离开。
在那个瞬间,我做好了选择:狮子是一个这么的强大而美丽的物种!而当我得知非洲野外仅存三万头狮子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应该做点什么来帮助它们。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去拯救狮子的话,它们很快就会从我们身边消失。而如果没有狮子,不敢想象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于是我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星巴”,以时刻提醒自己非洲狮所面临的生存危机。
回到中国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狮子的习性及其现状。2011年,我辞去了在重庆的工作,去到非洲。让妻子理解我的决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毕竟只有屈指可数的女人能够同意丈夫辞职离家,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了收入来养家糊口。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非洲是一个炎热、贫穷而且危险的地方。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我不想让父母担忧,所以抵非后也没有告知他们,相反,我常常会说自己在伦敦、巴黎或是纽约过得很好。因为这些相对安全的城市是生活工作的好地方,如此便可让老人家放心。善意的谎言持续了近两年,直到2012年的一天,爸妈在东非动物大迁徙的电视直播里看到了我,我才不得不向他们坦白。我是带着对狮子的满腔热血来到非洲大地的,虽然准备工作并不是特别充分,可那时的我早已38岁,没办法再继续等待。

我要特别感谢乔治•夏勒博士,他在我进退维谷的时候给了我非常重要的支持。他研究狮子和其他野生动物的传奇生涯也激励着我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而乔治、乔伊·亚当逊二人和狮群的关系是让我最终去到非洲的又一助推力。有很多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和动物保护者在非洲工作,但他们没有一个是中国人。我最开始的打算是加入其中一个组织,参与拯救狮子的工作,并有基本的工资保障,但是他们觉得中国人喜欢象牙角和犀牛角,根本不在乎野生动物保护。更有甚者,是在我第一次尝试使用脸书的时候,有两个瑞典人到我的主页留言,让大家都提防着中国人。我们素未谋面,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指责所有的中国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在那个时候已经在大熊猫、老虎和亚洲象保护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这让我倍感失落,甚至有了放弃梦想的想法。乔治博士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给了我及时的鼓励,在内罗毕我又和乔治•亚当森的助理托尼•菲茨约翰见面,他同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和经验,鼓励我要勇敢面对所有的问题和挑战。随后我去到马赛马拉,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以增加对当地居民的了解,尤其是弄明白他们目前的生活需求以及他们同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

我清楚地知道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不是一个短期工程,它不是接近动物、写篇论文然后回到大学拿到博士文凭这么简单,而是只能通过给当地社区提供稳定的利益保障,让他们一同积极参与进野保工作才能得以实现。
如果没有肯尼亚、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朋友的帮助,我不可能熬过最艰难的那段时间。2011年9月,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的注册成立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很可能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创立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的目标是为中国人搭建一个共同参与非洲野保工作的平台。如今,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的故事,我们也得到了更多的帮助。
在过去的8年里,马拉野保基金会持续的努力和贡献赢得了来自海内外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签署协议、参与共同项目、捐赠反盗猎装备以及教育项目等系列野保行动的开展,我们成为了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署(Kenya Wildlife Service)、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M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奥肯耶保护区(Olkinyei conservancy)、东非野保协会(Eastern African Wild life Society)、“拯救大象”组织(Save the Elephants)、“守望动物”(GameWatcher)是的关键合作伙伴。
直到今天我也丝毫无悔当初的决定,因为我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通过和政府部门、当地社区还有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合作,为拯救狮子的活动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我的梦想成真了,我得以跟狮子一起度过更多的美好时光!
仍旧记得在2011年,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署(KWS)兽医多米尼克博士和我一同治愈了一头伤势严重的年轻雄狮,它重新站起来时竟回头注视了我们好几秒才离开。我不确定它的行为是否是在表示“感谢”,但我能确认,人与狮子之间完全可以和谐共处。

狮子不会欺骗我或者是攻击我,所以于我而言,跟它们呆在一起比跟人相处轻松多了。我会在黄昏时分驱车看望它们,它们有时会很有默契地从灌木里出来。我享受和它们在一起的时间,它们也不介意在我身边吃吃喝喝、玩乐睡觉。小狮子喜欢和我玩捉迷藏,开车的时候它们会跟着我,当我回过头看时它们却又停下脚步,装作望向另外一个方向。
狮群会时不时拜访我们的营地,有时候甚至会逗留好几天,但最好还是和它们保持一定距离,毕竟这些家伙都不是由我们亲手养大的。奥肯耶保护区可能是非洲看到野生狮子最好的地方。我们每天巡逻两次,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狮子,如果看不到,那就必须晚上一直等待听到狮吼声才能入眠。
奥肯耶现在有两个狮群,一个新狮群,来自附近的保护区。领头的是三个雄狮,年龄在6岁左右,Dengo, 刀疤和凯撒。另外还有三只母狮以及9只幼崽。它们主要生活在奥肯耶的南部,以伊坡鹏溪流的中下游地区为核心栖息地。但这段时间(2019年8月),三只雄狮的巡逻范围已经覆盖到了奥肯耶的北部边界。以前的狮群,是莱姆尼狮群,也是由3头雄狮领衔(Batian, Senteo以及Ololana),包括4只母狮和4只幼崽。因为新狮群的入侵,这个狮群已经被迫北迁,离开保护区,隐藏在离边界约6-8公里的地域。

100年前的非洲大陆上生活着大约20万头野生狮子,而现在这个数字骤降至3万,这一切都要归因于动物栖息地流失和人狮冲突。作为非洲稀树草原和森林系统中的重要物种,狮子在生态平衡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它们为平衡绝大多数食肉、食草动物的数量,提高基因质量做出了贡献。如果狮子的生存状况良好,就意味着非洲大草原上其他动物的情况也是相对平衡的。
我们能不能拯救狮子和其他濒危动物,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确保其栖息地的安全。建立更多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是完成目标的最好方法,因为这是唯一一种行之有效的、可持续的途径来使野生动物和当地居民共同受益。过去7来,我们一直同奥肯耶保护区保持密切合作,提高村民的收入和福利,扩大就业,支持和提高野保巡逻站和巡逻员的装备能力,为当地社区修建防狮围栏以缓解人狮冲突,资助修建学校、教堂、帮助妇女和儿童发展、来改善教育质量、提高野保意识。

为了从生态旅行和野保经济中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目前越来越多的马赛人愿意主动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队伍中来。由于自由、安全生活的区域有了保障,包括狮子在内的保护区濒危动物数量有增长趋势,但是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全球变暖、人口爆炸、过度耕牧、工业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都使得野生动物栖息地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威胁。
国际合作的缺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野保工作的开展。在帮助非洲拯救野生动物栖息天堂的问题上,联合国和一些富裕国家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是时候让我们团结一心来共同面对这些来自于环境和动物生存危机的挑战了。归根到底,不管来自于哪个国家,最终我们都将走向人类的共同命运。
我不确定我们的努力能不能够保证狮子在这个星球上继续存活下去,但我相信不管怎样,我都会竭尽所能去帮助它们。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