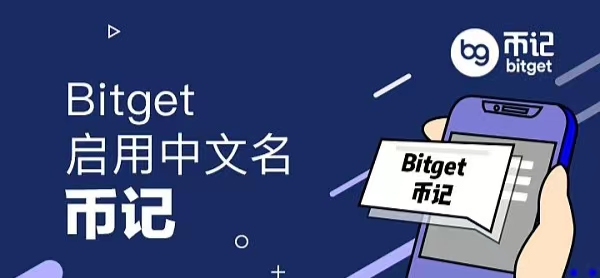王丰辉(资深金融从业者)
我曾论述过,推动银行转型终究要诉诸于管理者的选择、决断,甚至某些情况下,管理者可以腾挪的空间也极其有限。主要在于,转型、变革这样的事情,涉及到组织、资源、流程的重塑,在银行体系内,动资源就是动奶酪,张三掌控范围内的资源,哪怕张三用不好,也很难轮到李四用,这就是无处不在的摩擦成本和交易成本。
如此,最有效、最直接,或者说最温和的方式,反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慢慢寻求一种平衡,在不触动组织根基的前提下资源最优配置,这也是目前大多数银行在推进的转型方式。
但是,对正在推进中的转型,银行各个层级的评价是天差地别。你去问高层,高层会说“转型一直是我们的战略”;你去问中层,中层会说“掣肘太多、举步维艰”;你去问员工,员工大概率会说“转个毛~”
这些评价并非主观臆测,不过耳濡目染罢了。虽有少数银行略好一些,但也仅仅是略好一些。
这种不同的评价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目前银行转型的真相:高层以为自己在推进转型,但仅仅限于“战略”推进,难以穿透到实践层面;中层即使想转型,也身在局中无能为力,受限于职责边界和资源边界;而员工,尤其是一线员工,从人性角度讲,更关注转型给自身带来了什么,能力成长了?还是荷包鼓涨了?根据自然法则,越是规模庞大的群体其个体越是渺小,能引来噱头,但引不来切实关注,评价转型效果一个的“良心”纬度,是看看转型是否对员工带来改变,更要极力避免某些“为了转型而转型”所导致的员工苦不堪言。
那么,难道高层不英明神武吗?有一个极其政治正确的判断:高层一直英明神武。所有人都要承认,但凡走到高层,又致力于推动转型的人,其能力要超越99.99%的人,为你我所仰望。但银行转型之路为什么这么艰难,荆棘丛生?
让我们从这个问题抽身出来,喝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试想三个道理。

首先,过往既是你的依仗,更是你的枷锁。
一个人从籍籍无名走到功成名就,成为大众眼中的“成功人士”,必然有一套指导其行为的、且经其验证有效的“方法论”。一开始只是尝试,一次有效之后,两次有效之后,N次有效之后,这种行事方式就成为习惯,上升到准绳,最后固化为这个人的价值观。这个时候,有人蹦出来跟他讲道理,说,“你这一套不行,得换换脑筋了”,他要是瞅你一眼,他就输了,郭德纲老师也讲过类似的段子。
在神话传说中,能修成“大成真人”者,皆是身心内外洗练纯净、不迷不惘、应为即是愿为,什么意思?正是因为其某一方面信念的坚定,才成就今天的道果,这是其一切成就的根基。来个野道人,说你这信念是错的,还是换个吧。这叫什么?这叫坏人道基、生死之仇。二话不说,一道掌心雷,打杀了事。
这个道理,放到企业经营,也是一样。企业的立身之本是市场、技术、资源、流程、文化。在一个企业之初,其资源和技术,支撑其谋求一个细分市场,满足这个细分市场中的客户需求,慢慢发展,技术进步、资源积累、客户深耕,企业的主要利润,必然维系于某一个细分市场客群或某几个细分市场客群,其业务、产品、技术也必然聚焦于这些客群,倾听他们的意见,与客户一起成长。企业这样做对不对?太对了;企业管理者英不英明?太英明了。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也就与这些客群捆绑了,业务和产品由衣食父母决定,流程也得配合衣食父母的节奏,甚至你的文化、价值观都要与衣食父母相合。
这样的企业会失败吗?这样的企业的管理者会黯然吗?不好意思,会,例如诺基亚、摩托罗拉。
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循序渐进、正道成功的逻辑,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处在没有技术突变的时代,社会生产力在渐进式迭代,什么叫渐进式?就是可预期。那么什么叫不可预期呢?例如,微信替代短信、触屏替代键盘、数码替代胶卷。引用《创新者的窘境》中的定义,“破坏性技术”,指的并不是多么先进的技术,而是指这种技术代表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价值主张,本质上不是技术的变化,是认知和理念的变化。原来手机真的可以不带键盘,原来数据真的可以评估授信,原来银行真的可以没有网点。
我们要仔细瞅瞅这个词“截然不同的价值主张”,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种新技术所呈现的业务、产品,跟现在已经成功的你,跟你的企业,跟你的市场客群,直直白白的三观不合。少男少女都知道,如果三观不合,恋情是要告吹的。
很不幸,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破坏性技术”频现的时代。

其次,转型是不可预见的,是超低性价比的。
有人会说,不就是“破坏性技术”嘛,如果没啥技术门槛,已经上规模的企业怎得做不来?安排七八个小弟,分分钟搞定。
如你是当地豪强,家有良田千顷、娇妻美妾,路遇一乞丐,蓬头垢面、食不果腹,又有个野道人跳出来告诉你,这乞丐其实是当朝宰辅失落在外的纯种衙内,明天就认祖归宗,你现在上去跟他决斗,只要你胜了,他明天的一切都是你的,若你输了,你现在的一切都是他的。你怎么办?你肯定像看智障一样看着这个道人,然后喊出七八恶奴,将其胖揍一顿。
这个故事虽然恶俗,但道理却朴实无华,面对“破坏性技术”的企业也是这般处境。微信没有起来之前,谁能看到?iPhone4发布之前,谁能看到?即使看到了,也是“破坏性技术”的初期、萌芽,你能像乔布斯一样固执己见吗?你又能投入多少资源?你的企业能跟你一起驶入未知的前路吗?不要当事后诸葛亮,这也是我对所谓“最佳实践”不屑一顾的原因,不过是一套PPT卖多家而已。
转型的方向,从来都不清晰,本质上是无法预见的。有银行从业不服,说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方向很清晰啊。这其实是假象,那只是“数字化”这三个字清晰,这叫噱头清晰,但实际上,整个行业对“数字化”这个概念都很难达成一致。你去问一百家银行的行长,能问出一百个数字化的战略阐述;你去同一家银行问一百个人,能问出一百个数字化的理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在银行推进数字化的时候,选不同的人牵头,都能衍生出不同的数字化转型平行宇宙。甲牵头就这样转,乙牵头就那样转,相差了亿万光年。
这就是转型的“不可预见性”,这个概念请大家记住,后面我会再提,认识到这一点,转型才有希望。
前文也提到,一个企业在市场上历经风雨二三十年,有其固定利润来源,把利润拆开来看,收入是结构化的,有30%来自A市场A客群,有一二三部门人员靠此吃饭,有30%来自B市场B客群,有四五六部门人员靠此吃饭,有10%来自C市场C客群,有七八九部门靠此吃饭,等等。在这种结构之下,在这种惯性之下,这个企业的流程、财务、风险、制度,这个企业的决策链条和市场灵活性,其实都是由ABC市场的ABC客群决定的。
这个时候,你跑来告诉企业,说有个新技术、新产品、新业务,可以覆盖原来我们不曾涉足的D市场D客群,现在不好说,但未来一定可以提供30%以上的利润,只不过我们的流程、财务、风险、制度,需要改换一下三观?你怎么办?
不要拍脑袋想当然,觉得自己向来与时俱进、卓尔不群,向来“擅长创新”,我们拿实际案例说事儿。
案例一,快捷支付刚起来的时候,有哪家银行预见其现在了?没有,我那时恰逢其会,第三方支付与银行之间一波波关于快捷支付的口水战,我也出力不少。那时银行在想什么?首先监管层面是看不到依据滴,其次快捷支付风险太大了吧,再次这个对业绩指标也没什么价值,当然也有眼光深远者看到了“账户之争”的本质,银行会被“过顶传球”,尤其是银行的总行层面,大都是反对的。但快捷支付还是起来了,突破口在各家银行的分支行,快捷支付对某个分支行而言,带来的是赤裸裸的存款沉淀,你看,银行总行、分行的利益诉求也是不一样的。
案例二,余额宝出现之前,各家银行也都在卖货币基金,谁想着把体验做到极致,把流动性做到T0?听说,是某家银行的创意,但最终还是落地到了互金机构。并且,余额宝上线没几天,也有家银行加班加点两周搞定。但上线前一天,零售部老总找行领导哭诉“冲击存款”,还是不了了之。
案例三,二维码支付,在市场酝酿期,除了头部两家地主着力拓展之外,不少银行尤其还有大行,在快速跟进。但上面来了一纸文件,让停一停。银行特别老实,就真停了。但是有人没停,把“主扫”模式改为“被扫”模式,继续攻城掠地。如今看看,二维码支付市场,还有银行啥事?
案例四,长尾客群的消费信贷,没征信的白户,银行看得上吗?银行本来是看不上的,还够不着普通信用卡的门槛,没抵押,没房产,甚至工作也不怎么高大上,再说纯基于线上授信也没做过啊,风险想想就不可控,这要是逾期不良了,催收和核销的逻辑都不一样,按照现有的核销制度,靠都靠不上。
我们总是高估新事物的风险,而低估旧事物的风险,好像旧事物的风险完全在自己掌控范围内一样。之前由于现金贷泛滥、数据违规,再加上疫情冲击,又有些老成持重的人站出来说,“你看,你看,怎么着,我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通过数据对这些人群做风控、做授信,的确不靠谱。”
但历史潮流浩浩汤汤,我们再也看不到庞大的ENIAC,再也看不到小灵通,再也看不到可当作防身武器的诺基亚,而今,智能客服,已经几可以假乱真,数字员工,已经可以言笑晏晏,再也回不去“The Good Old Days”,从心理学上讲,并不存在真的美好旧时光,只是有人今日不爽罢了。
如果我们可以穿越,让一个今时今日的人,回到八九年前,在银行大声疾呼,一定要自己做快捷支付,守住账户,守住存贷汇的三分天下;一定要做余额宝,抓住存款搬家的主动权;一定要做长尾客户,每一个长尾都是生存的根基,管用吗?最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一切都不会变化。
在社会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拥有资源者拥有话语权,已经有了“鞋”,已经有了“碗”,为什么要去尝试“不确定性”?的确,无论快捷支付、余额宝、二维码支付、消费信贷,是技术多先进吗?不是,他们的出现,无一不是对既定市场分配、资源分配的挑战,都是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初时,我们都觉得是小打小闹,不值一提,此时银行是放不下身段的,并且,再庞大的组织,再庞大的银行,也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组成,让个体怎么做判断?我们都晓得,在投资中最稀缺的就是“确定性”,华尔街无数投行大佬愿意为确定性买单,不确定性意味着“赌博”,从人性上考量,你会去赌博吗?只有光脚的才会去赌博。
对,只有光脚的才会去赌博,这句话,也请大家记住,本文暂不展开了,这其实隐含了谁才会是变革的真正核心。

再者,文化是保障,但也是束缚。
你去问每家银行,都号称有自己的文化,但这些所谓的“文化”,充其量都只是“口号”,文化不是想出来的,不是必须要押韵的,而是“做”出来的,是通过每一件件小事体现出来的。不了解文化如何而来,就不会了解文化如何而变。那么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是泱泱大国,上下五千年,有灿烂的文明,有醇厚的文化,自从打开国门之后,我们放眼看世界,受冲击最大的是科学技术的差异吗?不是,是文化的差异。关于导致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我看到很多论述,有的说是山川气候的区别,有的说是地理历史的更迭,有的说是农耕文化和航海文化的区别,有的说是宗教和信仰的区别,有的说是语言文字的区别,等等,都有道理,我们可以寻到一条脉络,文化是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跟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
我更愿意通过世事的演化来说事儿,有这么几个部落,以捕猎和采摘为生,经过几代生息之后,他们发现不能猎杀幼崽,否则这种动物没几年就灭绝,也不能把野果摘绝,否则没几年就无果可采,于是他们就约定:碰到幼崽一律放生,必要时还要提供保护;采摘时一棵树都要留十个果。这约定施行一段时间,还是有人违背,怎么办?几个部落商定了统一的处罚措施,这可能是法律的雏形。一代代下来,这些约定成了部落众人的行为习惯,他们还在放生幼兽时跳舞庆祝,慢慢演化为幼兽节和幼兽舞,少男少女们以十为美,求偶时以由十粒种子串成的项链为礼,这就是风俗,这也是文化。这种文化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他们生存的根基,代表着他们族群的利益。
什么情况下,文化会改变?什么情况下,文化要改变?其生存基础发生了变化或者受到了冲击。那几个部落不再以捕猎和采摘为生,驯化了动物,学会了种植,其核心利益不再需要保护幼兽、留下十果,可能过渡到土地面积、人口数量,这些又将引导形成新的行为习惯,新的风俗礼仪,新的文化养成。
一家企业也是如此,一方面,文化并不是凭空而生的,是历史决定论的,在慢慢壮大的过程中,起于资源、技术,捆绑于市场、客户,沉淀为流程、制度,成为全员时时刻刻的行为准绳,制度无法触及的地方,有文化如水流淌;另一方面,文化也不是凭空变化的,无论管理层把自己的文化“名词”改得多么朗朗上口,例如,“以客户为中心”、“鼓励不同的声音”,这些你没有就是没有,并不会因为墙上贴着你就有了。
文化是生长出来的,文化的改变也是生长出来的,只有你的产品、你的技术、你的流程、你的制度、你的奖惩处罚、你的人员激励本身就是“以客户为中心”、“鼓励不同的声音”时,不用贴在墙上,你的文化就是如此,所以,要改变文化,就要改变企业的利益约束、资源约束,乃至于改变企业的生存基础,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这一点,又跟转型这个词从概念上相合。什么叫转型,你原来在新南方学校讲课挣钱,现在到新北方学校讲课挣钱,这不叫转型,这叫跳槽;现在你不讲课了,你靠直播带货挣钱,这才叫转型,引入了原本所不具备的能力、形成了原来所不具备的资源禀赋,你的生存逻辑发生了变化。
回到银行再谈这个事情,自上而下的转型,本质上是这么一个命题:在原有的文化框架下,怎么生长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这里提一下事业部的逻辑,为什么现在推动银行转型的人们对事业部这种“创新尝试”不怎么敏感了?究其根本,在于,事业部的资源和组织的独立性到底有多大空间,也等价于其文化独立性到底有多大空间,如果事业部的基础生产资料还受制于人,就不可能完美得承载“破坏性技术”,就没有文化独立性,这种情况下,还不如在高层的指挥下,通过敏捷小组来谋求一个利益的平衡,起码通过小组实现了条线的雨露均沾。
其实敏捷小组只是过渡阶段,明茨伯格在《管理至简》中提过一个观点,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诞生的工厂制度、条线边界、部门分工,其实已经过时了,现在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应该是“非正规的、不定型” 临时委员会组织(adhocracy),随项目、产品成立,随项目、产品解散,这些人员并不在adhocracy之外还隶属于固定的部门。相比之下,大家也发现了,敏捷小组的问题,现在各家银行推行的敏捷小组,小组成员还隶属于固定的部门,敏捷小组的工作在其工资、考评、晋升中仅占一部分,敏捷也就必然受阻。

讲了这么些,不给点儿建议就像耍流氓了。我本想从战略、管理、容错、文化这四个角度来阐述观点,但发现不够深刻,那么我试着换个思考角度。
其一,战略是生长出来的。
前文论述过,面对“破坏性技术”,未来是无法预知的。银行以其过往八九年的战绩告诉我们,在面对“破坏性技术”时,就没有成功过,但银行从业千万不要沮丧,原工行董事长姜建清曾言,银行不是短跑,是马拉松,我们欣赏的是马拉松冠军。现代银行诞生了有近400年,短短八九年算不了什么,银行业必然长期存在,但每一代银行从业都有其时代使命,我们这一代银行从业所面临的,就是数字化冲击之下的兴衰。
一些银行特别喜欢搞战略,搞规划,这本不是坏事情,但从这八九年的变迁看,所有的三年规划几乎都可以束之高阁,一是规划只能规划“渐进性技术”,也就是看得见的,渐进式有什么可规划的,你规划也是那样,不规划也是那样,还能翻出花来?二是规划从不关注细节,也没有市场灵敏度,并且好多规划都是定性的,不是定量的,“定性”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力发展、积极拓展、加快建设等致力于用最多的文字传递最少的信息的化石语言。三是,你没办法规划看不见的市场和业务,本来就不在你的预见之内,而我们恰恰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有人会举杭州马老师的例子来反驳,说什么“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你看看,有人能预见。马老师的确相信,但他相信的是数字技术的力量,相信的是我们这个风云迭起的时代,但他绝对无法预见支付宝、天猫、菜鸟,以及今天的阿里帝国,如果我们看《蚂蚁金服》这本书,会清晰得看到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坎坷崎岖,遇事做事罢了。还有深圳的马经理,几次三番QQ卖不出去,最后才“砸”到自己手里,成就今天的腾讯,你觉得,他能预见吗?不要用事后的心态看问题,事件中的当事人,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由此,我们或许才明白,转型、变革、应对“破坏性技术”,在变化的时代,我们无法提出一个战略,来规划无法预见的事情,也从没有可以清晰指导三五年的路径,那么,我们的战略和计划,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关于学习、发现的战略,如何在市场中学习,如何在实践中发现。
就拿数字化转型来说,没有人可以预见五年、十年之后的数字化银行将呈现的状态,但我们如果相信“数字化”这个大方向,那么我们的战略可以是,数字化一切可以数字化的“存量”,如何用数字化洞察客户,如何用数字化挖掘市场,如何用数字化重塑运营,但是这个粒度的预见仍然是没有意义的。银行的经营就像人生一样,每天都面临无数个选择,而所有的梦想、所有的未来,都在一个个选择之中,我们最应该做的,我们只能做的,是“如何保障每一个选择尽可能正确“。
这就像小学生一样,面对纷至沓来的知识,如何学会并做对?银行面对纷至沓来的名词噱头、市场机会、外部诱惑、内部摩擦,如何辨别是非并抓住线索?打造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组织什么特点?去除存量思维,不要动不动就说“原来怎样怎样”、“一直怎样怎样”;保持空杯心态,倾听并接纳不同意见,尤其是来自实践者的意见;保持好奇心,大胆尝试,哪怕错了;不断调整,在调整中寻找适配的路径。这其实就是学习、发现、成长的过程。
在银行的转型中,因为会碰到很多“新”,阻力往往来自你身边的存量,还没做过就觉得风险高,还没做过就急于否定,还没做过就指手画脚,还没做过就界定边界。一边口口声声要创新,一边却极力回避对原有稳定性的任何威胁,这种心态使得很多公司对创新可能带来的机会和利润都视而不见。
打造学习型组织其实非常艰难,谁会“打心底”承认自己有可能是错的,尤其在自己擅长的领域、N年的从业资历,谁会倾听一下“反对意见”。请大家注意“打心底”这个词,就是无论身处高层还是中层,是自发、自愿、自觉有这种认知,而非装出这种样子。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高层是否会在中层面前,中层是否会在员工面前,坦承,“这个方向我也看不清楚,还没有你们专业,先小步试一试吧。”
战略固然重要,但我从不认为存在一个有效的三年或五年战略,真正的战略是十字路口的一个个选择,是在“眼前的存量+眼前的冲击”之下做出的判断,由此,最重要的是“生长”出正确的战略,由此,最重要的是打造学习型组织。

其二,有效的管理是信息共享。
我自己也带团队,但我鼓励的不是“请示”,而是“报备”,也就是说,只需告诉我将怎么处理事情就行,而不必请示到底怎么处理。但这有一个前提假设,假设同事们处理事情的水平基本不低于我自己来处理的水平。如何实现?
首先管理者要明白一些事情,你比员工高明在哪儿?为什么你自认为同一件事情,你处理起来比员工处理得更好?员工智商也不比你低,为什么处理不好?我发现,判断一件事情处理得好不好,先看对这件事情的定位和态度,是拒绝、主导、配合还是敷衍,这是大方向,员工与管理者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其次才是你是强硬拒绝,还是委婉拒绝等具体执行时的诸多细节,而员工与管理者的差距在这块较小,其实有差距也没关系,因为这主要体现个人做事风格。面对一件事情,到底如何定位,到底持何态度,本质上跟能力无关,只与你所掌握的信息量有关。
放到银行中,针对一件事情如何处理,信息来自多个维度,例如监管的、同业的、行领导的、其他部门的、本部门职责边界的、本部门战略方向的,等等,这些维度的信息,对管理者而言,获取更容易,而恰恰是这些维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如何对事情定位;除上述维度之外的,事情进展、当前细节、接口交互、技术实现、素材佐证等等,对事情本身定位影响不大。我在日常工作中,不时向员工宣导这个观念,要想把事情处理好,就要把围绕这件事情上下左右前后的信息拿到手,然后再落地行动,如果信息掌握不全,事情就会处理不好。
基于信息共享的视角,管理者如果想让自己更轻松,想让自己从繁琐中解放出来,最好的方式,反而是共享信息,而非隔离信息。明茨伯格说,拒绝共享信息,常常是为了通过障眼法来囤积权利。
在上文中也说过“敏捷小组”,敏捷小组的本质是权利下放,试想一个事事需要请示的产品经理,如何敏捷?而权利下放再深入挖掘一下,其实也是信息的下放,需要管理者把自己掌握的信息同步给小组成员,因为管理者由于职位而掌握一些特殊的信息渠道,这些信息一般意义上理解,可能来自管理者的更上一层,如果管理者不把这些信息共享,权利下放也没有意义。
无论是敏捷小组、部门,还是部门之间、总分行之间,在转型中的很多障碍体现为条块壁垒、利益摩擦,无论我们再怎么幻想,科层制和条块短时间内无法改变,而以数字技术为底层的信息共享或许可以解决部分问题,数据面前人人平等。而模棱两可的描述,不把真实的信息、数据呈现出来,这不是源于对数据的沉迷,而是源于对权利的沉迷,因为我们终究会发现,如果你我所掌握的信息一致,那么我们调动的资源也将一致,这才是数据的革命性,数字化的革命性。

其三,失控带来无穷活力。
我家有女,也一直思考子女教育的问题。如果你把她管得比较严,坐卧行走、一板一眼,她就容易循规蹈矩。别人会说,这孩子怎么呆呆的?如果你完全不管,那她就疯了,上房揭瓦、任性妄为。所以,我自己总结下来,一方面要正面管教,引导行为礼貌;其他方面,只要定一两条底线,只要她不去触碰,就随她去,甚至你还可以鼓励随她去。这种让一部分失控的方式,貌似是妥协、放松了,但换来的却是她的活泼生动、天性解放。
我在部门管理中也是如此,我比较喜欢“无为而治”,甚少对员工过多干涉,哪怕有些事情做得并不让我满意,我也不会出言批评,因为没有触碰部门的原则问题,让他们放手施为,比较可喜的是,他们给了我太多惊喜。
在网络金融这个领域,虽然我一直不断夯实自己的专业性,但实际上像数据、体验、审美、营销、文案、视频等,他们的想法和创意要比我靠谱得多,乃至于在我事先并无安排的情况下,推进了很多事情,有人主动联系并营销大客户,有人把客户交互大幅提升,有人做的事情获奖了,有人接了市里的研究项目。我们部门是两级管理,员工之上还有各团队负责人,从表面上看,员工这个层面基本上是失控状态,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才是网络金融从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者,本应该有的组织的样子。如果不这样处理,事事都要过我,都要经过我的安排,员工就会失去工作的乐趣和成就感。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论述过,这次技术革命终将带来个人的崛起,我们的生产模式,不能再以劳动力、人力成本这样的视角看待员工,而应是知识主体、人力资本这样的视角。这儿可以提一句,如果一家银行的转型不能增加员工的成就感,其转型必然是失败的。
凯文凯利在《失控》中用大量篇幅、许多例子来阐述失控的价值,没有失控,就没有人类的进化,没有技术的发展,没有生态系统的演化。生物从上一代到下一代,基因有遗传、有变异,可能99%的基因都是一脉相承,乃至更高99.95%,有0.5%或者1%的变异,那么这种变异一定是好的吗?可不一定,你看看武大郎和武二郎。这种变异对生物而言是失控的,无法预判,无法选择,但正是这微小概率的变异,正是这微小概率的失控,才造就了地球生物圈的多姿多彩,否则,我们还是单细胞呢。
在人机围棋大战的热度渐消之后,DeepMind的科学家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Mastering the game of Go without human knowledge》,里面重点谈到AlphaGo Zero所采用的深度学习算法。这个算法模仿了人类如何探索世界,探索一下就获得一个反馈,正反馈就加强,负反馈就降低,但是到底往哪些方向探索呢?算法中有个小细节,耐人寻味,它对未知的探索增加了权重,鼓励算法去探索未知,貌似让算法“失控”,但是却带来了整体算法效率的最优。
有一家民营银行,在数据风控方面做得还可以,我向其请教,他说一点儿也不神秘,我们的模式就是AB测试,流量进来之后95%给主模型A,留5%给辅模型B,我们不断去调整B模型,什么时候B超过A了,我们就把B切换为主模型,再留5%给新的辅模型,再来一轮循环。我们也不能确定辅模型到底怎样,只能一遍遍的试验,让其“失控”,只有“失控”,我们才能发现更优的模型,才能一遍遍迭代。
这个道理放在银行转型中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们一遍遍强调要小步快跑、要试错、要包容,这样并非要彰显管理者的气度和胸怀,而是必须如此,这就像“战略是生长出来的”一样,你无法预期什么是更优的,但你又必须不断前进,硬着头皮去寻找转型的新思路、新组织、新产品、新业务,只能让一部分“失控”,“失控”的这部分虽然占比可能比较小,但却是持续不断的活力来源。我听说在某些大厂,不管自己手中有一张船票还是半张船票,都有一些小组、团队处在失控”状态。

末了,照应一下本文的主题,我是要谈管理的,管理者要正视自身的枷锁、承认未来的不可预见、看到存量文化的束缚,在转型实践中,是否有战略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正确”的前瞻性战略是不存在的,是一步步生长出来的,要想办法让信息在组织内共享,要刻意让一部分失控,等等。有人会说,你这还是有鸡汤性质,不给勺子呀,到底如何操作呢?
在这个时代,我们已无法奢望The Good Old Days那些英雄式的管理者,因为数字化的本意,变革的本意,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英雄,《易·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如群龙无首,则人人如龙。这个时候,如果仍有管理者存在,那么他的角色如何定位?
我将其定位成:点燃者,点燃每一个人的潜能。我在这方面还略有些心得体会,我在会上高呼“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于是我见证了员工论坛的上线;我极力倡导学习型组织,于是见证了“青年大讲堂”的落地;我引导青年员工分享讨论,于是见证了一个个敏捷小组成立;我鼓励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于是见证了许多年轻员工的文章获奖。见识和见证是不一样的,见识是“你知道飞机会上天”,见证是“你亲自参与了飞机上天”。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预见,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就像有一根蜡烛,你将其点燃,有光照亮了四野;就像有一根弦,你轻轻拨动,有声音悠扬入耳;就像有一湖水,你扔个石子,有涟漪圈圈漫延;就像有一把枪,你扣动了扳机,让子弹飞,且飞一会儿。
对,就是这样,变革中的管理者,要有勇气让子弹飞,更要有耐心让子弹飞一会儿。
全文完。
本文转自公众号“莫道寻常”(mdxunchang),已获作者授权。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