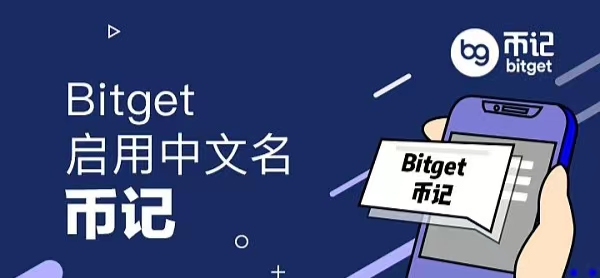无数人的情绪和命运,曾随虚拟货币的走势和政策变动瞬息万变。
3月的深圳,在一辆出租车上,许英龙向我展示了一场简短、微型的社会实验。
那是午夜的南山区,下班高峰期仍在持续,网约车排队200位起步,路上的车流如碎步前行。“师傅,您知道比特币吗?”刚结束了一场商业谈判的许英龙,在回酒店的途中,突发奇想地抛给司机一个问题。
“电视报纸上听说过,没怎么了解”。司机的回答简洁平和,既不驳乘客面子,又能快速把这个不感兴趣的话题结束。
“师傅,您开了几年车了?”显然,许英龙还想继续聊下去。
司机说,“十几年咯,从小伙子变成大叔了”。
“如果在十年前,您花2美元买一个比特币,放到现在,就变成38万人民币了”。
话音未落,红灯,停车。司机转头,用不可思议的眼神望向许英龙,“比特币是什么?”
许英龙试图用这个实验证明,“这就是大多数人对比特币的认知。他们对比特币是什么其实无所谓,对区块链也一知半解,但他们对赚钱有兴趣”。
这种对金钱的盲目追逐,大多由狂热开始,以一片狼藉收尾。
“无论是出租车司机、带着热钱闯入区块链领域的投机者,还是跟风并妄想财富自由的年轻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如果给大家提一些投资建议,第一条就是:一切挣到自己口袋的钱,都是认知的变现,在任何领域,不要试图突破自己的认知而当了一颗韭菜”。
说完这段话,88年出生的基金管理人许英龙,回到了中洲万豪酒店的客房。88年出生的我,哼着五条人的《深圳的街头》回到隔壁小路边的汉庭。
几个月后,一语成谶。
3月的北京,几日沙尘侵袭,似眼镜上蒙了灰尘,看不清说不明,几日又晴空万里,豁然开朗。
许英龙在北京的主场,位于南二环菜市口附近。几处临街四合院,应是近些年翻建,其中一座,几年前被他接手。
2021年,随着比特币交易价格突破六万美元,许英龙的四合院变得热闹起来,上门“取经”的拜访者络绎不绝。
许英龙又嗅到了似曾相识的,热烈但危险的味道。
许英龙对区块链的认识,始于2011年第一次接触比特币,那时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留学,周围的同学已通过比特币进行游戏点卡交易。
但彼时的许英龙,对此兴趣不大,他痴迷于摄影,这是20岁出头的他看世界的方式。他花了一年,每天拍一张照片,出版了摄影画册《光影成歌 英伦365摄影日记》。
他在画册的最后里写到:“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踩着滑板鞋梳着小辫子的少年了,纵然广交天下好友,对酒当歌,嬉笑怒骂,插科打诨,但身体中的另外一个自己总会飘到我的头顶,他静静看着我,他什么也不说,他神情落寞,他若有所思。”
和许多人设为“白手起家”的青年才俊不同,面对媒体,许英龙从不避讳父亲对自己的支持,留学归国后,凭借资本、人脉、知识储备,他在传统行业里快速崭露头角。
许英龙真正进入了区块链领域投资是2017年。那是比特币的上一轮牛市,比特币涨幅超过1600%,一度突破2万美元大关。
无数人的情绪,随着比特币的走势起伏波动。众多资本涌入,狂热的炒币者、招摇撞骗的人也开始入场,随之而来的是比特币大跌,数字货币进入熊市……
面对一边倒的负面舆论,几个月前还谈笑风生的人信心崩塌,有人退出了,更有甚者面对无法翻身的命运,提前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在2021年的6月,许英龙再次见到了类似的场景,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已今非昔比。他习惯在“区块链”后面加上技术两个字。他相信,世界是由技术驱动的。
币圈的浮躁消散,给了许英龙冷静和蛰伏的时间,他与有着一样想法的人走到一起,继续深研区块链技术、研究高级的算法,他相信,除开数字货币,区块链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都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从深圳回到北京,我与许英龙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四合院地下室一间略显幽暗却极富腔调的房间里。
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和一位摄影圈的朋友对话——是的,我几乎快忘记他还有摄影师这一身份了。
2017年,这位摄影师将13个以太坊ETH(数字货币)交给朋友,投资了一个“空气币”项目——这是没有实体项目支撑的虚拟币,没有任何价值,纯粹靠营销手段,用“高利润”、“只涨不跌”等营销话术,引诱投机者进场接盘,然后撒手离场,不管场内投机者死活。
“你该找他把损失要回来!这肯定得要回来!”许英龙有些激动,“你算算他骗了你多少钱”。
见对方有些犹豫,许英龙又继续开导,“把这些钱要回来,多买几个徕卡镜头不好么?”
这句话让摄影师下定决心,要去法院起诉对方——和在深圳与出租车司机对话一样,许英龙总能掐准对方的情绪变动。
许英龙厌恶在区块链领域浑水摸鱼的人,打着数字货币的旗号招摇撞骗的人,尤其在币圈牛市的时候,这类人就特别多。
“如果哪一天大家谈起‘区块链’色变,那就是这些骗子导致的,而真正的区块链技术,是在进步和发展的”。
送走朋友后,许英龙让试酒师为他倒了一杯威士忌,闻了闻,抿上一小口,通常一杯威士忌可以喝一整晚。这个房间的一面是酒墙,威士忌占了大多数。他说,圈子里的人大多好这一口。
其中一些酒很有趣,是区块链比特币的定制款,每一瓶都有自己的编号,一款酒只生产210瓶,是为致敬2100这个数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同年11月1日,一个自称中本聪的人在网络上发布了比特币白皮书《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陈述了他对电子货币的新设想——比特币就此面世。
2009年1月3日,比特币创世区块诞生。
简而言之,在货币膨胀的年代,中本聪把比特币定义为通货紧缩的货币,比特币总量被限定在2100万枚,全球各地的人可以用计算机的算力挖掘比特币,俗称“挖矿”。
中本聪规定:比特币最小可以细分到小数点后8位小数(聪),比特币每10分钟产生一个区块,每个区块发行50个比特币(矿工奖励),每21万个区块后,每个区块的产量减半。所以,每四年,区块发行的比特币将减半。
与之对应的是挖矿的计算难度越来越大,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大——有科学家估算,如果把比特币视作一个国家,它将位列全球耗电量最大的前30国。
对资源的过度消耗,让“挖矿”饱受诟病,也为后续来自国家层面的打击,埋下了伏笔。
2021年6月,铁拳终于落下。
继内蒙古、青海等地之后,加密货币矿场聚集的四川,也开启清退挖矿项目。在这场币圈的“浩劫”发生前,虽然已有一些预兆和传闻,但矿工们明显并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由于地理优势与能源优势,在中国西南,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加密货币矿场。有资本的人,不管用什么渠道,小则几十台,多则几百台,把自己的矿机托管在这些矿场,由专人维护。每月除掉电费后,按照加密货币的交易价获取利润。
可实际上“矿圈”真正的核心地区是在深圳,在大湾区。这里有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芯片开发公司,这里才是矿圈乃至整个区块链的金字塔顶端。
在深圳,我们曾认识了一位矿机制造商,在当时的交谈中,他对自己的产品保持着乐观和信心——在国家对“挖场”打击之前,他刚解决了矿机的产量问题。
在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后的第二天,许英龙早早起床,和深圳的商学院同学约在深圳人才公园晨跑。当年他以基金管理人的身份去商学院学习,结交了不少朋友。
来自传统行业的同学们,当年并不理解许英龙为什么只关注区块链技术领域投资,但这次深圳之行,他成为了座上宾。跑完步,在南山区的一座高尔夫球场里,他们教许英龙打高尔夫,许英龙给大家普及什么是区块链技术,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区块链领域的投资。
除了这个高尔夫局,许英龙在深圳两天,参加了六个商业饭局,其中包含一顿早餐,跑了五家他投资的公司,约见了三波客户。
原本许英龙还想在深圳多呆几天,但他必须回北京,投资全赛道的他不会错过最近几个月的区块链新领域——2021年3月11日,美国加密艺术家beeple的NFT艺术品“THE FIRST 500 DAYS”在佳士得拍卖上拍出了6295万美元的高价,NFT加密艺术品这个概念在圈内火爆刷屏。
将自己定义为基金管理人的许英龙,不愿错过每个布局的机会。
在许英龙从深圳回到北京没几天,我跟着他参加了一场在北京798举行的一场名为《虚拟生境》的加密艺术展,这是全球首个大型线下展,他在此找寻布局区块链NFT的机会。
这场线下展的策展人是一位“90后”艺术家孙博涵,也是许英龙的好朋友。
孙博涵和我聊起了自己在做的事,“NFT是(Non Fungible Token)的缩写,意为非同质化代币,它是一个架构在区块链上的加密数字权益证明。简单来说,它是一个放在云端的产权和保真证书”。
“NFT这种权益证明不同于加密货币,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分割的,一旦形成就永远不可更改。而对于NFT与加密艺术品也有区分,NFT相较于加密艺术品更具有门槛,比如我们传统的一幅国画,把它上链后拥有独一无二的编号,它就成为了加密艺术品。但NFT的创作是从逻辑上就与传统艺术不同,它是用算法进行创作的一种形式,最终它在区块链中就是一串数字代码,这是它的本体。到了线下的物理世界,它就可以变成图像化进行展览”。
但即便他用最简洁的语言来告诉我什么是NFT,什么是加密艺术品,我仍旧有些云雾缭绕。
孙博涵从小就和数字、计算机打交道。他记得在2002年,电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他就被妈妈送去学习Photoshop。初中毕业,他从南京来到了北京,就读央美附中,随后考入央美油画专业并保研。
因为儿时的经历,他说自己比其他艺术生对数字的敏感度要高。当研究生导师为他介绍加密艺术时,他一下子就听入迷了,由此开始了自己的NFT之旅。
最开始,他只是一位创作者,随着对这个领域的逐渐深入,他觉得这个领域大有可为。在上一轮熊市期间,他也坚持做面向国内用户的加密艺术品交易平台。
如果抛开NFT、区块链、加密艺术品这些词语,整场展览更像是一场当代艺术展,兼具了神秘、有趣、互动和思考。在展览开幕前,孙博涵估计每天有小几百人能进来看看,他就满意了。但事实上,来的人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开幕前三天,观众量达到日均两三千人。
此次展览,孙博涵也得到了“THE FIRST 5000 DAYS”展出的授权,可以让更多的参观者在物理世界中近距离看到NFT艺术品拍卖的“巅峰之作”。而他和团队成员化身讲解员,不厌其烦地为每一波进来的参观者讲述什么是NFT,什么是加密艺术品,就如同他对我所讲的那样。
从传统艺术走向加密艺术,孙博涵觉得排在第一位的仍旧是艺术,他相信NFT终有支配艺术品交易市场的那天。作为摄影师的许英龙,对此也深信不疑。
孙博涵加入了北京朝阳区的一个文创培育项目,500多平米的场地将在半年后变为全球最大的NFT线下展示店。他旁边是李雪琴的工作室,后面是流浪地球的电影制作公司。
他的《虚拟生境》展下一站将移师上海,然后一站一站做下去。
许英龙依然认为,区块链“未来可期”,但肯定不只是挖矿、炒作和投机。
但他也不确定,在将来,它将以哪一种形式呈现,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还是成为他想象中的那个像“三体”一样信息透明的区块链世界。
这个未来,只有这个行业里最终被“剩”下的那些从业者才能见证了。
来源:腾讯新闻
编辑:张恒 刘梦鸽 吕瑞天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