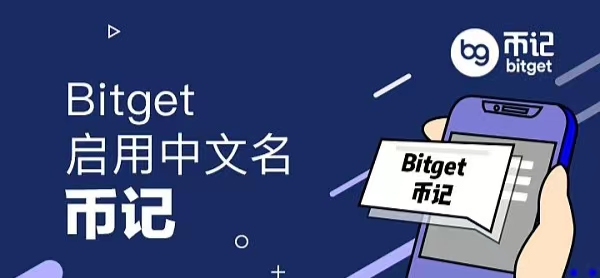爱缘何不再动人
少年的我,对爱情之向往,最初由《牛郎织女》一则故事而萌发。当年哥哥高一的“文学”课本上便有,而且配着美丽的插图。
此前母亲曾对我们讲过的,但因并未形容过织女怎么好看,所以听了以后,也就并未有过弗洛伊德的心思产生,倒是很被牛郎那一头老牛所感动。那是一头多无私的老牛啊!活着默默地干活,死了还要嘱咐牛郎将自己的皮剥下,为能帮助牛郎和他的一儿一女乘着升天,去追赶被王母娘娘召回天庭的织女……
曾因那老牛的无私和善良落过少年泪,又由于自己也是属牛的,更似乎引起一种同类的相怜。缘此对牛的敬意倍增,并巴望自己快快长大,以后也弄一头牛养着,不定哪天它也开口和自己说起话来。
常在梦里梦到自己拥有了那么一头牛……
及至偷看过哥哥的课本,插图中织女的形象就深深印在头脑中了。于是梦里梦到的不再是一头牛,善良的不如好看的。人一向记住的是善良的事,好看的人,而不是反过来。
以后更加巴望自己快快长大,长大后也能幸运地与天上下凡的织女做夫妻。不一定非得是织女姊妹中的“老七”。“老七”既已和牛郎做了夫妻,我也就不考虑她了。另外是她的姐姐和妹妹都成的。她很好看,她的姊妹们的模样想必也都错不了。那么一来,不就和牛郎也沾亲了么?少年的我,极愿和牛郎沾亲。
再以后,凡是在我眼里好看的女孩儿,或同学,或邻家的或住一条街的丫头,少年的我,就想象她们是自己未来的“织女”。
于是常做这样的梦——在一处山环水绕四季如春的美丽地方,有两间草房,一间是牛郎家,一间是我家;有两个好看的女子,一个是牛郎的媳妇,一个是我媳妇,不消说我媳妇当然也是天上下凡的;有两头老牛,牛郎家的会说话,我家那头也会说话;有四个孩子,牛郎家一儿一女,我家一儿一女。他们长大了正好可以互相婚配……
我所向往的美好爱情生活的背景,时至今日,几乎总在农村。我并非一个城市文明的彻底的否定主义者。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连自己也解释不清自己。有一天下午,我在社区的小公园里独自散步,终于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之一:公园里早晨和傍晚“人满为患”,所以我去那里散步,每每于下午三点钟左右。图的是眼净。那一天下着微微的细雨,我想整个公园也许该独属于我了。不期然在林中走着走着,猛地发现几步远处的地上撑开着一柄伞。如果不是一低头发现得早,不是驻步及时,非一脚踩到伞上不可!那伞下铺着一块塑料布,伸出四条纠缠在一起的腿。情形令我联想到一只触爪不完整的大墨斗鱼。莺声牛喘两相入耳,我紧急转身悄悄遁去……没走几步,又见类似镜头。从公园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凡见六七组矣。有的情形尚雅,但多数情形一见之下,心里不禁骂自己一句:“你可真讨厌!怎么偏偏这时候出来散步?”
回到家里遂想到——爱情是多么需要空间的一件事啊!城市太拥挤了,爱情没了躲人视野的去处。近年城市兴起了咖啡屋,光顾的大抵是钟情男女。咖啡屋替这些男女尽量营造有情调的气氛。大天白日要低垂着窗幔,晚上不开灯而燃蜡烛。又有些电影院设了双人座,虽然不公开叫“情侣座”,但实际上是。我在上海读大学时的七十年代,外滩堪称大上海的“爱情码头”。一米余长的石凳上,晚间每每坐两对儿。乡下的孩子们便拿了些草编的坐垫出租。还有租“隔音板”的。其实是普通的一方合成板块,比现如今的地板块儿大不了多少。两对儿中的两个男人通常居中并坐,各举一块“隔音板”,免得说话和举动相互干扰。那久了也是会累的。当年使我联想到《红旗谱》的下部《播火记》中的一个情节——反动派活捉了朱老忠们的一个革命的农民兄弟,迫他双手高举一根苞谷秸。只要他手一落下,便拉出去枪毙。其举关乎性命,他也不过就举了两个多小时……
上海当年还曾有过“露天新房”——在夏季,在公园里,在夜晚,在树丛间,在自制的“帐篷”里,便有着男女合欢。戴红袖标的治安管理员常常“光顾”之前隔帐盘问,于是一条男人的手臂会从中伸出,晃一晃结婚证。没结婚证可摆晃的,自然要被带到派出所去……
如今许多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虽然相对减缓了城市人的住房危机,但也同时占去了城市本就有限的园林绿地。就连我家对面那野趣盎然的小园林,也早有房地产商在觊觎着了。并且,前不久已在一端破土动工,几位政协委员强烈干预,才不得不停止。
爱情,或反过来说情爱,如流浪汉,寻找到一处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并不那么容易。白天只有一处传统的地方是公园,或电影院;晚上是咖啡屋,或歌舞厅。再不然干脆臂挽着臂满大街闲逛。北方人又叫“压马路”,香港叫“轧马路”。都是谈情说爱的意思。
在国外,也有将车开到郊区去,停在隐蔽处,就在车里亲爱的。好处是省了一笔去饭店开房间的房钱,不便处是车内的空间毕竟有限。
电影院里太黑,歌舞厅太闹,公园里的椅子都在明眼处,咖啡屋往往专宰情侣们。
于是情侣们最无顾忌的选择还是家。但既曰情侣,非是夫妻,那家也就不单单是自己们的。要趁其他家庭成员都不在的时间占用,于是不免有些偷偷摸摸苟苟且且……
当然,如今有钱的中国人多了。他们从西方学来的方式是在大饭店里包房间。这方式高级了许多,但据我看来,仍有些类似偷情。姑且先不论那是婚前恋还是不怎么敢光明正大的婚外恋……
城市人口的密度是越来越大了。城市的自由空间是越来越狭小了。情爱在城市里如一柄冬季的雨伞,往哪儿挂看着都不顺眼似的……
相比于城市,农村真是情爱的“广阔天地”呢!
情爱放在农村的大背景里,似乎才多少恢复了点儿美感,似乎才有了诗意和画意。生活在农村里的青年男女当然永远也不会这么感觉。而认为如果男的穿得像绅士,女的穿得很新潮,往公园的长椅上双双一坐,耳鬓厮磨;或在咖啡屋里,在幽幽的烛光下眼睛凝视着眼睛,手握着手,那才有谈情说爱的滋味儿啊!
但一个事实却是——摄影、绘画、诗、文学、影视,其美化情爱的艺术功能,历来在农村,在有山有水有桥有林间小路有田野的自然的背景中和环境里,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魅力。
艺术若表现城市里的情爱,可充分玩赏其高贵,其奢华,其绅男淑女的风度气质以及优雅举止;也可以尽量地煽情,尽量地缠绵,尽量地难舍难分,但就是不能传达出情爱那份儿可以说是天然的美感来。在城市,污染情爱的非天然因素太多太多太多。情爱仿佛被“克隆”化了。
比之《牛郎织女》《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中的爱情其实是没有什么美感的。缠绵是缠绵得可以,但是美感无从说起。幸而那爱情还是发生在“园”里,若发生在一座城市的一户达官贵人的居家大楼里,贾宝玉整天价乘着电梯上上下下地周旋于薛林二位姑娘之间,也就俗不可耐了。
无论是《安娜·卡列尼娜》,还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几乎其他的一切西方经典小说,当它们的相爱着的男女主人公远离了城市去到乡间,或暂时隐居在他们的私人庄园里,差不多都会一改压抑着的情绪,情爱也只有在那些时候才显出了一些天然的美感。
麦秸垛后的农村青年男女的初吻,在我看来,的确要比楼梯拐角暗处搂抱着的一对儿“美观”些……村子外,月光下,小河旁相依相偎的身影,在我看来,比大饭店包房里的幽会也要令人向往得多……
我是知青的时候,有次从团里步行回连队,登上一座必经的山头后,蓦然俯瞰到山下的草地间有一对男女知青在相互追逐。隐约能听到她的笑声。他终于追上了她,于是她靠在他怀里了,于是他们彼此拥抱着,亲吻着,一齐缓缓倒下在草地上……一群羊四散于周围,安闲地吃着草……
那时世界仿佛完全属于他们两个,仿佛他们就代表着最初的人类,就是夏娃和亚当。我的眼睛,是唯一的第三者的眼睛。回到连队,我在日记中写下了几句话是:
天上没有夏娃,
地上没有亚当。
我们就是夏娃,
我们就是亚当。
喝令三山五岳听着,
我们来了!
……
这几句所篡改的,是一首“大跃进”时代的民歌。连里的一名“老高三”,从我日记中发现了说好,就谱了曲。于是不久在男知青中传唱开了。有女知青听到了,并且晓得亚当和夏娃的“人物关系”,汇报到连里。于是连里召开了批判会。那女知青在批判中说:“你们男知青都想充亚当,可我们女知青并不愿做夏娃!”又有女知青在批判中说:“还‘喝令三山五岳听着,我们来了!’来了又怎么样?想干什么呀……”
一名男知青没忍住笑出了声,于是所有的男知青都哈哈大笑。
会后指导员单独问我——你那么篡改究竟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唉,我想,在这么广阔的天地里不允许知青恋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白白浪费。
……
爱情或曰情爱乃是人类最古老的表现。我觉得它是那种一旦框在现代的框子里就会变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东西”。城市越来越是使它变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框子”。它在越接近着大自然的地方才越与人性天然吻合。酒盛在金樽里起码仍是酒,衣服印上商标起码仍是衣服。而情爱一旦经过包装和标价,它天然古朴的美感就被污染了。城市杂乱的背景上终日流动着种种强烈的欲望,情爱有时需要能突出它为唯一意义的时空,需要十分单纯又恬静的背景。需要两个人像树,像鸟儿,像河流,像云霞一样完全回归自然又享受自然之美的机会。对情爱城市不提供这样的时空、背景和机会。城市为情爱提供的唯一不滋扰的地方叫作“室内”。而我们都知道“室内”的门刚一关上,情爱往往迫不及待地进展为什么。
电影《拿破仑传》为此作了最精彩的说明:征战前的拿破仑忙里偷闲遁入密室,他的情人——一位宫廷贵妇正一团情浓地期待着他。
拿破仑一边从腰间摘下宝剑抛在地上一边催促:“快点儿!快点儿!你怎么居然还穿着衣服?要知道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是的,情爱在城市里几乎成了一桩必须忙里偷闲的事情,一件仓促得粗鄙的事情。
我常想,农村里相爱着的青年男女们,有理由抱怨贫穷,有理由感慨生活的艰辛。羡慕城里人所享有的物质条件的心情,也当然是最应该予以体恤的。但是却应该在这样一点上明白自己们其实是优于城里人的,那就是——当城里人为情爱四处寻找叫作“室内”的那一种地方时,农村里相爱着的青年男女们却正可以双双迈出家门。那时天和地几乎都完全属于他们的好心情,风为情爱而吹拂,鸟儿为情爱而唱歌,大树为情爱而遮阴,野花为情爱而芳香……
那时他们不妨想象自己们是亚当和夏娃,这世界除了相爱的他们还没第三者诞生呢。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和一个姑娘相爱已三年了。由于没住处,婚期一推再推。他曾对我抱怨:“每次和她幽会,我都有种上医院的感觉。”
我困惑地问他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说:“你想啊,总得找个供我俩单独待在一起的地方吧?”
我说:“去看电影。”
他说:“都爱了三年了!如今还在电影院的黑暗里……那像干什么?不是初恋那会儿了,连我们自己都感到下作了……”
我说:“那就去逛公园。秋天里的公园正美着。”
他说:“还逛公园?三年里都逛了一百多次了!北京的大小公园都逛遍了……”
我说:“要不就去饭店吃一顿。”
他说:“去饭店吃一顿不是我们最想的事!”
我说:“那你们想怎样?”
他说:“这话问的!我们也是正常男女啊!每次我都为找个供我俩单独待的地方发愁。一旦找到,不管多远,找辆‘的’就去。去了就直奔主题!你别笑!实事求是,那就是我俩心中所想嘛!一完事儿就彼此瞪着发呆。那还不像上医院么?起个大早去挂号,排一上午,终于挨到叫号了,五分钟后就被门诊大夫给打发了……”
我同情地看了他片刻,将家里的钥匙交给他说:“后天下午我有活动,一点后六点前我家归你们。怎么样?时间够充分的吧?”
不料他说:“我们已经吹了,彼此腻歪了,都觉得没劲透了……”
在城市里,对于许多相爱的青年男女而言,“室内”的价格,无论租或买,都是极其昂贵的。求“室内”而不可得,求“室外”而必远足,于是情爱颇似城市里的“盲流”。人类的情爱不再动人了,还是由于情爱被“后工业”的现代性彻底地与劳动“离间”了。
情爱在劳动中的美感最为各种艺术形式所欣赏。
如今除了农业劳动,在其他一切脑体力劳动中,情爱都是被严格禁止的。而且只能被严格禁止。流水线需要每个劳动者全神贯注。男女混杂的劳动情形越来越成为历史。
但是农业劳动还例外着。农业劳动依然可以伴着歌声和笑声。在田野中,在晒麦场上,在磨坊里,在菜畦间,歌声和笑声非但不影响劳动的质量和效率,而且使劳动变得相对愉快。
农业劳动最繁忙的一项乃收获。如果是丰年,收获的繁忙注入着巨大的喜悦。这时的农人们是很累的。他们顾不上唱歌也顾不上说笑了。他们的腰被收割累得快直不起来了;他们的手臂在捆麦时被划出了一条条血道儿;他们的衣被汗水湿透了;他们的头被烈日晒晕了……
瞧,一个小伙子割到了地头,也不歇口气儿,转身便去帮另一垄的那姑娘……
他们终于会合了。他们相望一眼,双双坐在麦铺子上了。他掏出手绢儿替她擦汗。倘他真有手绢儿,那也肯定是一团皱巴巴的脏手绢儿。但姑娘并不嫌那手绢儿有他的汗味儿,她报以甜甜的一笑……
几乎只有在农业劳动中,男人女人之间还传达出这种动人的爱意。这爱意的确是美的。又寻常又美。
我在城市里一直企图发现男人女人之间那种又寻常又美的爱意的流露,却至今没发现过。
有次我在公园里见到了这样的情形——两拨小伙子为两拨姑娘们争买矿泉水。他们都想自己买到的多些,于是不但争,而且相互推挤,相互谩骂,最后大打出手,直到公园的巡警将他们喝止住。而双方已都有鼻子嘴流血的人了。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望到了那一幕,奇怪,他们一人能喝得了几瓶冰镇的矿泉水么?后来望见他们带着那些冰镇的矿泉水回到了各自的姑娘们跟前。原来由于天热,附近没水龙头,姑娘们要解热,所以他们争买矿泉水为姑娘们服务……
他们倒拿矿泉水瓶,姑娘们则双手捧接冰镇矿泉水洗脸。有的姑娘费用了一瓶,并不过瘾,接着费用第二瓶。有的小伙子,似觉仅拿一瓶,并不足以显出自己对自己所倾心的姑娘比同伴对同伴的姑娘爱护有加,于是两手各一瓶,左右而倾……
他们携带的录音机里,那时刻正播放出流行歌曲,唱的是:
我对你的爱并不简单,
这所有的人都已看见。
我对你的爱并不容易,
为你做的每件事你可牢记?
……
公园里许多人远远地驻足围观着那一幕,情爱的表达在城市,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往往便体现得如此简单,如此容易。
我望着不禁想到,当年我在北大荒,连队里有一名送水的男知青,他每次挑着水到麦地里,总是趁别人围着桶喝水时,将背在自己身上的一只装了水的军用水壶递给一名身材纤弱的上海女知青。因为她患过肝炎,大家并不认为他对她特殊,仅仅觉得他考虑得周到。她也那么想。麦收的一个多月里,她一直用他的军用水壶喝水。忽然有一天她从别人的话里起了疑点,于是请我陪着,约那名男知青到一个地方当面问他:“我喝的水为什么是甜的?”
“我在壶里放了白糖。”
“每人每月才半斤糖,一个多月里你哪儿来那么多白糖往壶里放?”
“我用咱们知青发的大衣又向老职工们换了些糖。”
“可是……可是为什么……”
“因为……因为你肝不好……你的身体比别人更需要糖……”
她却凝视着他喃喃地说:“我不明白……我还是不明白……”
而他红了脸背转过身去。
此前他们不曾单独在一起说过一句话。
我将她扯到一旁,悄悄对她说:“傻丫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他是爱上你了呀!”
她听了我这位知青老大哥的话,似乎不懂,似乎更糊涂了。呆呆地瞪着我。
我又低声说:“现在的问题是,你得决定怎么对待他。”
“他为什么要偏偏爱上我呢……他为什么要偏偏爱上我呢……”她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地重复着,随即双手捂住脸,哭了。哭得像个在检票口前才发现自己丢了火车票的乡下少女。
我对那名男知青说:“哎,你别愣在那儿。哄她该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
我离开他们,走了一段路后,想想,又返回去了。因为我虽比较有把握地预料到了结果,但未亲眼所见,心里毕竟还是有些不怎么踏实。
我悄悄走到原地,发现他们已坐在两堆木材之间的隐蔽处了——她上身斜躺在他怀里,两条手臂揽着他的脖子。他的双手则扣抱于她腰际,头俯下去,一边脸贴着她的一边脸。他们像是那样子睡了,又像是那样子固化了……
同样是水,同样与情爱有关,同样表达得简单、容易,但似乎有着质量的区别。
在中国,在当代,爱情或曰情爱之所以不动人了,也还因为我们常说的那种“缘”,也就是那种似乎在冥冥中引导两颗心彼此找寻的宿命般的因果消弭了。于是爱情不但变得简单、容易,而且变成了内容最浅薄,最无意味可言的事情。有时浅薄得连“轻佻”的评价都够不上了。“轻佻”纵使不足取,毕竟还多少有点儿意味啊!
一个靓妹被招聘在大宾馆里做服务员,于是每天都在想:我之前有不少姐妹被洋人被有钱人相中带走了,但愿这一种好运气也早一天向我招手……
而某洋人或富人,住进那里,心中亦常动念:听说从中国带走一位漂亮姑娘,比带出境一只猫或一只狗还容易,但愿我也有些艳福……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相见恨晚,各自遂心如愿。
这是否也算是一种“缘”呢?
似乎不能偏说不算是。
是否也属于情爱之“缘”呢?
似乎不能偏说不配。
本质上相类同的“缘”,在中国比比皆是地涌现着。比随地乱扔的糖纸冰棒签子和四处乱弹的烟头多得多。可谓之曰“缘”的“泡沫”现象。
而我所言情爱之“缘”,乃是那么一种男人和女人的命数的“规定”——一旦圆合了,不但从此了却男女于情于爱两个字的种种惆怅和怨叹,而且意识到似乎有天意在成全着,于是满足得肃然,幸福得感激;即或未成眷属,也终生终世回忆着,永难忘怀。于是其情其爱刻骨铭心,上升为直至地老天荒的情愫的拥有,几十年如一日深深感动着你自己。美得哀婉。
这一种“缘”,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当代,是差不多绝灭了。唐开元年间,玄宗命宫女赶制一批军衣,颁赐边塞士卒。一名士兵发现在短袍中夹有一首诗: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
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
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
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
这位战士,便将此诗告之主帅。主帅吟过,铁血之心大恸,将诗上呈玄宗。玄宗阅后,亦生同情,遍示六宫,且传下圣旨:“自招而朕不怪。”
于是有一宫女承认了诗是自己写的,且乞赐离宫,远嫁给边塞的那名士兵。玄宗不但同情,而且感动了。于是厚嫁了那宫女。二人相见,宫女噙泪道:“诗为媒亦天为媒,我与汝结今身缘。”边塞三军将士,无不肃泣者。试想,若主帅见诗不以为然,此“缘”不可圆;若皇上龙颜大怒,兴许将那宫女杀了,此“缘”亦成悲声。然诗中那一缕情,那一腔怜,又谁能漠视之轻蔑之呢?尤其“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二句,读来令人愀然,虽铁血将军而不能不动儿女情肠促成之,虽天子而不能不大发慈悲依顺其愿……
此种“缘”不但动人、感人、哀美,而且似乎具有某种神圣性。
宋仁宗有次赐宴翰林学士们,一侍宴宫女见翰林中的宋子京眉清目秀,斯文儒雅,顿生爱慕之心。然圣宴之间,岂敢视顾?其后单恋独思而已。
两年后,宋子京偶过繁台街,忽然迎面来了几辆皇家车子,正避让,但闻车内娇声一呼“小宋”,懵怔之际,埃尘滚滚,宫车已远。回到住处,从此厌茶厌饭,锁眉不悦,后作《鹧鸪天》云: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栊,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此词很快传到宫中,仁宗嗅出端倪,传旨查问。那宫女承认道:“自从一见翰林面,此心早嫁宋子京。虽死,而不悔。”仁宗虽不悦,但还是大度地召见了宋子京,告以“蓬山不远”。问可愿娶那宫女?宋子京回答:“蓬山因情而远,故当因缘而近。”于是他们终成眷属。
诗人顾况与一宫女的“缘”就没以上那么圆满了。有次他在洛阳乘门泛舟于花园中,随手捞起一片硕大的梧桐叶子,见叶上题诗曰: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
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第二天他也在梧桐叶上题了一首诗:
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
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
带往上游,放于波中。十几日后,有人于苑中寻春,又自水中得一叶上诗,显然是答顾况的:
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
顾况得知,忧思良久,仰天叹曰:“此缘难圆,天意也。虽得二叶,亦当视如多情红颜。”据说他一直保存那两片叶子至死。情爱之于宫女,实乃精神的奢侈。故她们对情爱的珍惜与向往,每每感人至深。
情爱之于现代人,越来越变得接近着生意。而生意是这世界上每天每时每刻每处都在忙忙碌碌地做着的。更像股票,像期货,像债券,像地摊儿交易,像拍卖行的拍卖,投机性,买卖性,速成性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司空见惯。而且,似乎也越来越等于情爱本身了。于是情爱中那一种动人的、感人的、美的、仿佛天意般的“缘”,也越来越被不少男人的心女人的心理解为和捡钱包、中头彩、一锨挖到了金脉同一种造化的事情了。
我在中学时代,曾读过一篇《聊斋》中的故事,题目虽然忘了,但内容几十年来依然记得——有一位落魄异乡的读书人,皇试之期将至,然却身无分文,于是怀着满腹才学,沿路乞讨向京城而去。一日黄昏,至一镇外,饥渴难耐,想到路途遥遥,不禁独自哭泣。有一辆华丽的马车从他面前经过而又退回,驾车的绿衣丫鬟问他哭什么?如实相告。于是车中伸出一只纤手,手中拿着一枚金钗,绿衣丫鬟接了递给他说:“我家小姐很同情你,此钗值千金,可卖了速去赶考。”
第二年,还是那个丫鬟驾着那辆车,又见着那读书人,仍是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很是奇怪,便下车问他是不是去年落榜了?
他说不是的啊。以他的才学,断不至于榜上无名的。
又问:那你为什么还是这般地步呢?
答曰:路遇而已,承蒙怜悯,始信世上有善良。便留着金钗作纪念,怎么舍得就卖了去求功名啊。
丫鬟将话传达给车内的小姐,小姐便隔帘与丫鬟耳语了几句。于是那车飞驰而去,俄顷丫鬟独自归来,对他说:我家小姐亦感动于你的痴心,再赠纹银百两,望此次莫错过赴考的机会……
而他果然中了举人,做了巡抚。于是府中设了牌位,每日必拜自己的女恩人。
一年后,某天那丫鬟突然来到府中,说小姐有事相求——小姐丫鬟,皆属狐类。那一族狐,适逢天劫,要他那一身官袍焚烧了,才可避过灭族大劫。没了官袍,官自然也就做不成。更不要说还焚烧了,那将犯下杀头之罪。
狐仙跪泣曰:小小一钗区区百银,当初助君,实在并没有图报答的想法。今竟来请求你弃官抛位,而且冒杀头之罪救我们的命,真是说不出口哇。但一想到家族中老小百余口的生死,也只能厚着脸面来相求了。你拒绝,我也是完全理解的。而我求你,只不过是尽一种对家族的义务而已。何况,也想再见你一面,你千万不必为难。死前能再见到你,也是你我的一种缘分啊……
那巡抚听罢,当即脱下官袍,挂了官印,与她们一起逃走了……
使人不禁就想起金人元好问《迈陂塘》中的词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直教”二字,后人们一向白话为“竟使”。然而我总固执地认为,古文中某些词句的语意之深之浓之贴切恰当,实非白话所能道清道透道详道尽。某些古文之语意语感,有时真比“外译中”尤难三分。“直教生死相许”中的“直教”二字,又岂是“竟使”二字可以了得的呢?好一个“直教生死相许”,此处“直教”得沉甸甸不可替代啊!
现代人的爱情或曰情爱中,早已缺了这分量,故早已端的是“爱情不能承受之轻”了。或反过来说“爱情不能承受之重”。其爱其情掺入了太多太多的即兑功利,当然也沉甸甸起来了。“情难禁,爱郎不用金”——连这一种起码的人性的洒脱,现代人都做不太到了。钓金龟婿诱摇钱女的世相,其经验其技巧其智谋其逻辑,“直教”小说家戏剧家自叹虚构的本事弗如,创作高于生活的追求,“难于上青天”也。
进而想到,若将以上一篇《聊斋》故事放在现实的背景中,情节会怎么发展呢?收受了金钗的男子,哪里会留作纪念不忍卖而竟误了高考呢?那不是太傻帽儿了么?卖了而不去赴考,直接投作经商的本钱注册个小公司自任小老板也是说不定的。就算也去赴考了,毕业后分到了国家机关,后来当上了处长局长,难道会为了报答当初的情与恩而自断前程么?
如此要求现代人,不是简直有点儿太过分了么?
依顺了现代的现实性,爱情或曰情爱的“缘”的美和“义”的美,也就只有在古典中安慰现代人叶公好龙的憧憬了。
故自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从全世界的范围看,除了为爱而弃王冠的温莎公爵一例,无论戏剧中影视文学中,关于爱情的真正感人至深的作品凤毛麟角。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算一部。但是性的描写远远多于情的表现,也就真得失美了。《廊桥遗梦》也算一部。美国电影《人鬼情未了》是当年上座率最高的影片之一。这后两个故事,其实都在中国的古典爱情故事中可以找到痕迹。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它们是“移植”,但却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戏剧影视文学中关于爱与情的美质,倘还具有,那么与其说来自现实,毋宁说是来自对古典作品的营养的吸收。
这就是为什么《简·爱》《红字》《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以及《牛郎织女》那样的纯朴的民间爱情故事等仍能成为文学的遗产的原因。
电影《钢琴课》和《英国病人》属于另一种爱情故事,那种现代得病态的爱情故事。在类乎心理医生对现代人的心灵所能达到的深处,呈现出一种令现代人自己怜悯自己的失落与失贞,无奈与无助。它们简直也可以说并非什么爱情故事,而是现当代人在与爱字相关的诸方面的人性病症的典型研究报告。
在当代影视戏剧小说中,爱可以自成喜剧、自成闹剧、自成讽刺剧、自成肥皂剧连续剧,爱可以伴随着商业情节、政治情节、冒险情节一波三折峰回路转……
但,的的确确,爱就是不感人了,不动人了,不美了。
有时,真想听人给我讲一个感人的、动人的、美的爱情故事呢!不论那是现实中的真人真事,抑或纯粹的虚构,都想听呢……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