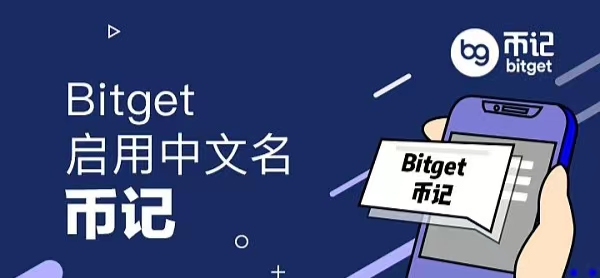河北省拥有一处在史学界举足轻重的研究平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这座宋史研究重镇能崛起于河北,要归功于已故历史学家、当代宋史学界泰斗漆侠。
漆侠祖籍山东,1953年,正逢而立之年的漆侠,因“历史问题”受到处分,调入天津师范学院(今河北大学前身),感念河北大学危难之际的“收留”,自此他扎根河北,在河北大学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教书匠”生涯,直至2001年去世都未曾离开。
走近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让我们共同追忆属于这座研究机构和它的奠基人漆侠的一段往事。
师从名师立志研究宋史
晚年漆侠。
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有一间专门的漆侠纪念室。纪念室进门左侧是一排书架,右侧是四张沙发椅,靠窗摆放着写字台,宽敞明亮的室内,一尘不染。
这一切,都是依照漆侠生前办公室的旧貌布置的。正对窗户的墙上,挂着漆侠的遗照,上书:“史苑巨擘,宋学泰斗,盛名垂千古;学界宗师,教坛昆仑,桃李竞芬芳。”
2001年,这位当代宋史学界的泰斗、原河北大学教授漆侠去世,消息震动史学界。
成为宋学泰斗的漆侠,在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史学之志。
1923年生于山东巨野的漆侠,自小就喜欢读历史故事、名人传记。
抗战爆发后,家乡沦陷。1941年,漆侠随山东流亡学生来到四川绵阳国立第六中学读高一,这一年漆侠18岁。到六中后,“对理工全无兴趣”的漆侠,大把的时间都耗在文史类书籍上。
高中期间,漆侠读完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皮瑞锡的《经学历史》、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
高中二年级的一次作文课上,当老师问及每位学生高中毕业后的志向时,漆侠说他的志向在于“立言”,要追随于司马子长(司马迁)。
这一志向虽饱含少年意气,却成了漆侠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1944年,漆侠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6年秋后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读三年级。
这个秋天,漆侠结识了日后的恩师,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宋史专家邓广铭。本来对毕业后学术方向有些迷茫的他,自此决定“追随先生(邓广铭)学习宋史”。
漆侠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了聆听恩师《宋史专题研究》第一堂课的情景。
“第一堂课,先生以鲁北话作为基本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清楚,而真正吸引人们的则是先生讲课的内容……先生从宋的立国形势,北有强邻契丹辽国,京都开封又系四通八达之地,由此论述宋代‘以兵立国’,以养兵作为基本国策。与此同时,对凡是有危害于专制统治的诸因素,‘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结果是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为历代所未有。先生对宋代立国规模的论述,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看,不仅是当时学术界绝无仅有的,而且这些论点,经住了历史的检验,愈益证明它的正确。”
1984年漆侠(左一)与老师邓广铭在香港参加国际宋史研讨会。
虽然选修了邓广铭的课,但漆侠起初并未与老师交谈过。促成漆侠踏上宋史研究之路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两人的几句对话。
“我考入大学之后……利用卡片抄录一些材料。期终考试时,我的这些卡片放在桌面上,先生经过时看了一些卡片,他笑着问我:‘你打算学宋史?’我说是。接着先生说:‘你有工夫可以到我家去。’自此,我总是隔些时候到先生家去,向先生提问。先生不但回答我提的问题,还指定我看哪些书。许多书是从先生家借的,除借之外,先生还给了许多书……充实了我的书架。”
1948年,漆侠大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成为邓广铭先生的第一名研究生。自此,漆侠开始踏上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宋史研究的学术道路。
专著填补宋史研究空白
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的漆侠(前排中)。
漆侠自20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投身史学研究,使其在史学研究中崭露头角的,是在宋史研究领域颇具开创意义的《王安石变法》一书。
至今,对于王安石变法进行科学、系统、全面研究的,业内首推漆侠。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但自南宋初年到晚清近八百年间,因为材料欠缺或研究者见识不高,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研究并客观评价王安石变法。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出现一个高潮。学者们开始运用近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以梁启超的《王荆公》影响最为持久。
20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了再评价,其中代表性成果之一,就是漆侠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一书,对北宋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借此揭示了王安石变法的广阔社会背景,阐明了变法的酝酿及其最终成熟原因,论证了新法的来源、内容、实质和变法过程中的复杂曲折的斗争,并且指出了变法最终失败的根源所在。
邓广铭也曾给予此书高度评价。他说,“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漆侠教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对于熙宁新法进行了认真探索,超越了前此所有的同类著作。”
《王安石变法》的出版,在海外也产生了较大关注和影响。
当时,日本、苏联的学者都为此书写过书评。漆侠的弟子、宋史专家陈峰,20世纪九十年代到德国慕尼黑大学访问时,该校一位汉学家听说他是研究宋史的,立即将一本出版于1959年的《王安石变法》拿了出来。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是漆侠的成名作,那么1987年、1988年出版的《宋代经济史(上下册)》则是他的代表作。
《宋代经济史》近百万字,是我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中的里程碑式著作,曾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作为史学类经典被中华书局《中国文库·新中国60年特辑》收录,也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宋代经济史》从人口、垦田、水利、经济作物、经营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赋税制度等方面,全面论述了两宋300余年间社会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全过程,重点研究了宋代农业生产、土地关系、手工业发展、国家专利制度、商业和城市经济、对外贸易、货币及经济思想等问题。
该书被史学界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大型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专著”,是“填补空白的奠基性巨著”,是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历史学家王曾瑜研究宋代经济史多年,《宋代经济史》出版后他曾写了一篇书评,称此书“集大成”。他在书评中写道:“人们喜欢用集大成一词形容某人的学术成就。我想,用此词形容《宋代经济史》一书,是当之无愧的。”
除了“集大成”的赞誉,在《宋代经济史》一书出版后,学界开始有“青出于蓝”之谓。
1987年,原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景戎华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称“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研究,近年来创获甚丰,特别是已经震动了素以治宋代经济史著称的日本史坛。漆氏乃邓氏之高足,可谓‘青出于蓝’。”
漆侠的同学、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守常,说漆侠“是同班同学中做学问的成绩最好的一个。(他)后来主要是研究宋史,特别是宋代经济史,其成就是超过了邓广铭先生的。”
高徒出于名师。在漆侠看来,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是站在了老师的肩膀上。
在回忆老师的文章中他讲道,20世纪宋代史学研究领域,“真正能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只有先生”,“先师邓广铭先生的研究给后人开创了广阔的道路,我们应当继承下来,并沿着这个途径继续探索,使此前的研究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晚年一手创建
“宋史研究第一重镇”
1987年漆侠(右一)在宋史研究室小院内与师生交流。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是国内宋史研究领域唯一的“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海内外宋史研究人才最集中、宋辽金史资料最丰富、宋史研究信息最灵通的科研机构,被誉为“宋史研究第一重镇”。
如此重要的学术研究平台,正是漆侠晚年呕心沥血、一手创建的。
1953年,正逢而立之年的漆侠因“历史问题”受到处分,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调入天津师范学院(今河北大学前身)。感念河北大学危难之际的“收留”,自此他扎根河北,在河北大学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教书匠”生涯,直至去世未曾离开。
1982年1月14日,经河北省高等教育局批准,在河北大学创建独立的科研机构宋史研究室,由漆侠任宋史研究室主任。
宋史研究室成员高树林回忆,初创的宋史研究室最初连固定办公地点都没有,创立半年多后,才搬入河北大学北院第一教学楼的一间办公室,后又搬迁至河北大学南院靠近学校礼堂的一所小院落。
有固定办公地点后,漆侠带领全室人员订购报刊、书籍,创建了书籍报刊资料室,并赴北京购买了大量研究宋史的基本书籍。为了充实资料室,漆侠甚至把自己购置的线装本《宋会要辑稿》等放到资料室,供师生查阅。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宋史研究室便是今天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前身,而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在漆侠的带领下不断深化。
台湾历史学者黄宽重评价漆侠对河北大学宋史研究的贡献时,借用台湾学人赞誉傅斯年创建中央研究院的评语,认为漆侠完成的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事业”。
漆侠长于史学研究,却并未因此耽误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他一直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培养了众多教学和科研人才。
1955年9月考入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后执教于河北大学历史系的王岸茂,清楚记得漆先生上课的情景:
“只见一个年轻人走上了讲台。穿的是很平常的棉衣和棉鞋,戴一顶旧棉帽子,一只耳朵在帽顶上覆盖着,另一只则耷拉在一边。这种随随便便的样子,在校园里还是第一次看见,感觉很特殊很新鲜。可是听了几节课后,都认为这个老师讲得好,史实清楚,观点明确,有条有理,讲课水平显然高得多。”
史学专家、漆侠的学生裴汝诚则感念学生时代老师寄给他的60元购书款。
1956年中华书局缩印出版了《宋会要辑稿》,征求预订。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的裴汝诚很想购买此书,但因经济困难一时无力购买,几经考虑后给自己的老师漆侠写了封信,说明想借钱购买此书。他很快收到老师的60元汇款和附信:“此书为研究宋史者所需之书籍,速购。”裴汝诚喜出望外,深受感动。
事实上,当时漆侠的家庭负担也很重,吃穿都十分节约,但助学生买书却毫不迟滞,慷慨解囊。
除了科研和教学之外,入校后不久漆侠便开始指导青年教师。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规定,每位来校或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都要接受一位“老教师”的指导。漆侠虽然年轻,却因为水平较高,被列入“老教师”之列。
漆侠在指导教师及他的研究生时,常常要强调基本功深厚的重要性。
在一份1989年的《教学工作总结》中,漆侠写道:“只学历史,学不好历史;只学宋史,学不好宋史。”“要在专(断代史)的基础上通(通史),要在通的基础上专。”“搞断代研究,必须以通史为基础;搞通史,必须以断代研究为基础。”“一个扎扎实实的基础,才能在史学上有所成就。养成一个好的学风,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向更远大的目标前进。”
斯人虽去,斯文犹存。漆侠的学术道路和建树,治史特色及品格,都将继续泽被学林。 (记者 李冬云 通讯员 王晓薇)
■相关
尊师重道 嘉惠学林
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在漆侠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漆侠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对老师的敬重与感激。特别是到了晚年,漆侠本人也需要别人的关怀照顾,可他心中还总是牵挂着自己的老师。
作为邓广铭培养的第一名研究生,生活中,漆侠面见恩师时总是毕恭毕敬,执弟子之礼。
漆侠弟子李华瑞对1991年8月北京举办国际宋史研讨会时,漆侠带其到北大朗润园邓广铭家中汇报会议议程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天进门落座后,漆侠师的恭敬和拘谨都在一声带有浓重山东乡音的紧张问候中传递出来,‘老师,您好,我是来给您汇报国际宋史研讨会的’,漆侠师一直前倾着身子面向邓先生,椅子只坐了前半截,汇报完一个问题,就问一句‘老师,这样行不行’。”
邓广铭晚年生病住院,漆侠不顾自身哮喘进京探望,并在邓广铭八十寿辰时,带病从保定赶往北京,为恩师祝寿。
但许多人并不知道,正是出于对恩师的敬重,漆侠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愿让他人知道自己是邓广铭的学生。
“1953年底,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中出了岔子,开会批判。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在一个时期之内,我既不愿意说自己是先生的学生,也不愿意别人知道我是先生的学生,唯恐有损先生的清誉。”漆侠在回忆恩师邓广铭的文章中,讲述了当时自己内心的惭愧与不安。
对于自己的大学老师、历史学家张政烺,漆侠也尊敬有加。
“1988年,我去济南参加山东大学博士生的论文答辩,碰上张政烺苑峰(字)先生。张先生虽然没有指导我论文,但他对我的厚赐终生不敢稍忘。我的心目中,苑峰师同恭三师(邓广铭)都是我的恩师。”漆侠曾这样讲道。
漆侠时常向后辈谈及老师张政烺学问上的博闻强记、造诣高深,以及自己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研究生时,老师对他的鼓励和帮助。
漆侠临终前办的最后一件事,是向自己的老师——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一良的家属起草一份唁电。然而,这封饱含对老师敬重和哀思的唁电还未发出,漆侠便与世长辞。 文/记者 李冬云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