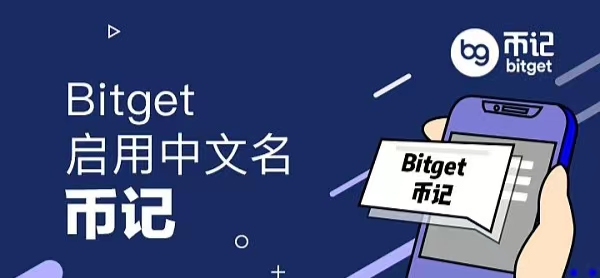张一兵
张一兵教授是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2007年, 他提出构境论思想后, 在学术界受到了较多非议。2009年之后, 张一兵进一步提出塑形、构式、构序和筑模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范式, 以建立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僭越式对接。最近, 本刊编辑就此问题专访了张一兵教授。现特整理发表这一访谈, 以期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深入探讨。
张琳 (以下简称“问”) :您是2012年第五届《哲学分析》论坛的“坛主”, 当时选的研讨题目是“回到事情本身何以可能”, 这让我想到您的构境论 (the theory of situating) 或许与重视情境 (situation) 的现象学之间有着某种关联?
张一兵 (以下简称“张”) :你会发现, 我在《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关于构境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逻辑承袭》里造了几个新词, 塑形、构式、构序和筑模, 并且分别英译为shaping、configurating、ordering和modeling。其实, 构境这个词的英译situating也已经包含了这种思考。你会发现, 王庆节教授在他的会议批评中用的是situation这个词, 我能感觉得到, 他对构境论的理解和批评是最接近原初语境的, 但不同的地方在于, 我已经把这个词改造成situating。他主要是看了《回到海德格尔》 (样稿本) , 他感到有兴趣, 但他并不同意我对海德格尔的解释。这个问题的发生是与我以前对海德格尔的一个错误判断相关。过去我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 (Sein) 这个概念, 先是从英译文中把它错误理解成海德格尔把现成性的名词动名词化为Being。Modeling这个词是皮格林教授用的。2010年我们曾请他访问南京大学, 在第八期《社会批判理论纪事》我们还会有一个皮格林教授的专题。他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最重要的代表, 属于当代的SSK (科学知识社会学) 中的最新思潮。他强调实践, 跟马克思比较接近。Modeling一词是他用的, 被我理解成model+ing。所以, 在《哲学研究》那篇文章中我把一些概念统统都动名词化了, 包括“劳动塑形”这个词,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查到马克思用的德文原文 (Formung) , 马克思文本的英译本里面是formation这个词, 而我当时英译用的是shaping。这个+ing想法是在我研究海德格尔哲学后发生的改变。
2007年以后, 当我确认了构境论在中国学术界的不可接受性以后, 我觉得要有一些大师来跟我一块言说。因为我已经发现, 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一直到海德格尔哲学中, 我所思考的一些线索在大师们思考过程中是真实存在的。Ausformung这个词在胡塞尔那里就出现过, 是形式显示中赋形的意思;海德格尔那里也有一批这样的重要概念, 除去Ausformung, 还有Gestalt (格式塔塑形) 与Ordnung (构序) , Situation也有, 在德文当中也是用作名词, 用作一个结果来区分的, 他是用Situation界划了另一个德文词, 不叫情境, 就是处境 (Lage) 的概念, 就是一个死掉的情境的概念, 他用Situation所代替的是德文里面的“Zusammenhung”, 我把它翻译成“关联与境”, 在汉译过程当中这些词全漏掉了。
我们这个团队, 现在准备慢慢做一件事情, 比如做马克思、海德格尔、阿多诺, 从德文里面去做;做阿尔都塞、福柯, 朗西埃、巴迪欧, 从法文里面去做。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深化, 是要从原文中重新回到马克思, 这可能是第二次回到马克思。因为, 第一本《回到马克思》, 大部分是在汉译的基础上, 那么, 这次希望我的后学们能够从德文语境重新回到马克思。然后, 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概念在德文中所具有的原初语境, 在从德语转译俄语, 俄语再转译汉语的过程中不复存在了。所以, 这次我在做海德格尔的时候, 每一个概念全部是重新用德文标注的, 这就避免了翻译当中, 15个老师15种翻法, 很混乱。我如果改译了, 就会做说明。
其实, 我觉得构境论与场境论观念关联性最大, 或者说构境论的重要来源, 实际上是格式塔心理学, 而不是现象学。我注意到,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共同受到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 特别是胡塞尔后来那个“时间现象学”里面大量用了一些对声音、对音响记忆的格式塔理解, 他在对内时间现象学分析中, 特别是声音延续的那一段讨论, 基本上是格式塔心理学场境论的一个结果。这部分内容, 实际上是非常深的一个主观构境方面。在《回到海德格尔》 (1) 这本书里, 我对海德格尔的场境意蕴观点做了一点阐发, 有的部分和我的构境论做了一点链接。我发现, 海德格尔从塑形的概念到构型的概念, 然后再到场境性呈现的格式塔的概念。比如海德格尔的1922年《那托普报告》中周围世界的场境存在观点, 其实阿伦特后来的劳动理论实际上和20年代海德格尔的讨论直接相关, 所以阿伦特后来能够理解海德格尔的重要思想变化, 从劳动上升为一种非劳动性的活动的概念。我想这个部分, 不是和梁康他们所解释的那条意识现象学的思路相关, 而是从现象学到海德格尔往另外一个“实际解释学”的方向走的那部分相关。所以, 大家读我关于海德格尔文本的理解会发现, 海德格尔很重要的一些观点和我的一些判断是接近的。通过这样一种策略性、隐性负载性的阐释, 实际上, 是想在一个与大师们的共有话语平台上让大家接受我所提出的构境论问题。
然后, 我正在写的《回到福柯》这本书也是如此, 在认真精读福柯的一些重要学术文本过程中, 我发现福柯很深刻的一些基本概念和重要观点, 在从法文到中文的转译中, 整个原初理解构境层就已经不存在了, 在文本的转译过程中丢掉了。比如, 福柯前期在《词与物》中多次使用的构序 (ordre) 概念, 他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提出的话语事件场 (champ desévénements discours) 的词组, 他的话语塑形 (formation discursive) 范式等, 中文都没有翻译出来。塑形这个概念, 我会在将来英文翻译当中不再用shaping这个词, 而是用formation这个词, 因为德文和英文里面是共同用这个概念来表达这一构境意义的。我注意到, 它是从亚里士多德形式—质料说里面一点点演变过来的, 形式内化为一种建构性的塑形的概念, 然后再到内部的构式 (configuration, 或构型) , 然后再到功能性的筑模。实际上, 在海德格尔那里和福柯的法文文本中比较多地用的是格式塔的概念。格式塔 (Gestalt) 概念, 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用了, 它也有一个复杂的前发生的过程。
我下一步工作还会有一些重要文本的工作 (广松涉、阿甘本、佐恩·雷特尔、波兰尼等) , 这些文本解读会和我自己的想法慢慢地靠近, 然后通过对话来创造一个和我自己思想的接近度。建构这个接近度, 我觉得非常困难。
问:从字面上来看, 我会把“构境”理解为“建构”+“情境”, 从而把“构境论”理解为情境建构理论。您的构境论是否是某种意义上的建构论?
张:我觉得, 从构境论的支援背景来看, 它更多的不是缘起于那种康德的图式建构说或狄尔泰的关系建构论的思想, 它可能已经是一种更深的格式塔式的场境论的思想。因为, 在康德那里, 先天综合构架的建构作用比较多地停留在外部赋形的逻辑关系中, 狄尔泰也是, 至多进展到海德格尔前期还在使用的那个结构与历史交合的Zusammenhung中。这个表示复杂关联性的建构性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也有, 它不是指A和B的关系或简单联系, 而是多重因素相互关联同时发生的一个场境过程。Zusammenhung就是“共同关联”, 但这个词在汉译中只是翻成了普通的“联系”。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那篇文章 (1) 中谈到, 狄尔泰的方法论自觉非常清楚, 他明确说, 我是要把系统论和历史建构结合到一块, 所以他的建构论是一个复杂关系体和一个历史建构的整合关系。但是, 他还没有从一般性的Zusammenhung走向海德格尔后来所讲的那个复杂的生命过程的在场。
这两年, 我对海德格尔和福柯的研读, 与我提炼自己、理清自己构境论的思想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我这里面要说一点, 在我理解海德格尔也好, 理解其他所有哲学家也好, 我都不是按照原有的那个西方哲学或者心理学原有人们已经给予的那个范式的逻辑框架去做, 我完全是按照我自己的思路来走的, 所以这种方式也反映了一个对所有传统领域的拒斥。
问:您将自己的构境论称之为“后文本学的方法”, 这里这个“后”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后”吧?您的构境论与后现代理论之间有着怎样一种关联?这一点您之前也有所涉及, 能否再略微展开讲一下。
张:好的。先说一下文本学研究的问题。文本学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提出来的, 当时是为了区别于传统斯大林模式中那种用原理观点反注经典文本的“原著研究”。除去我前面已经说过的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典籍文献诠释学的传统, 在当代西方学界, 还有从中世纪神学文本诠释学中发展而来的现代性文本研究方法———哲学解释学, 以及阿尔都塞式的文本研究。从总体上说, 《回到马克思》一书的文本研究方式还是属于现代性文本学的, 而我要从“思想构境”出发, 自然会得到一种不同于现代性文本学的研究方法。我在《回到列宁》一书的“作者的话”中, 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文本构境法解读”, 或是“思想构境论”。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回到马克思》中使用的现代性文本学解读法的一种超越, 我不再仅仅停留在现代性的文本学讨论域之中, 放弃了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那种对文本原初语境的逼近假相。甚至可以说, 我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了后现代文本学的合法地位, 也认同晚期巴特所说的“文本阅读不是还原, 而是创造性的生产”的观点。这是从文本学研究的视角看, 我与“后学”的某种关系。一般而论, 我对欧洲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后现代思潮”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但我会认真阅读他们的东西, 汲取其中批判话语中的积极成分。
问:那么, 构境论跟情境论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您看来, 构境论是否是情境论的一个升级版?
张:实际上, 构境论不是来自你所提到的所谓情境论。通常的理解中, 情境论会有教育学中的情境认知理论 (1) 、领导科学中的情境理论 (2) 和语言学中的情境语义学 (3) 等方面。但实际上, 我自己比较关注的倒是法国的情境主义 (Situationism) 思潮。在国内, 也是我们最早向学术界引介了法国的情境主义国际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 这是一个重要的先锋艺术流派, 我觉得这一思潮无论是对我们的艺术理论还是哲学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2006年, 我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率先主持翻译和出版了德波的《景观社会》。 (4) 最近, 我们会在第七辑的《社会批判理论纪事》刊登情境主义国际的很重要的一个论文集, 25万字, 从德波的文本到阿甘本等人的评论, 全部都有。另外还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情境主义的文本也都翻译过来了, 范内格姆的《日常生活革命》和德·赛托的《日常生活实践》两卷都已经出版。 (5) 虽然, 法国的情境主义思潮对我来说很重要, 但我的构境论想法跟他们还是不太一样。
依我的看法, 情境主义更多的是一种艺术情境论。德波自己主要是做电影的, 算得上是电影大师, 他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先驱。德波所建立的情境主义国际, 实际上是一个由不同流派的先锋艺术家组成的团体, 而且是一个激进的艺术团体, 因为, 他们的理论主张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叛。 (6) 情境主义国际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到70年代解散, 有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并且, 他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一定的关联, 在法国1968年发生的著名的“红色五月风暴”中, 情境主义国际的很多文本成为学生造反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他们很有名的一个概念就是“让想象力夺权”。他们自己的主要口号就是用了列斐伏尔的一句话, 即“让生活成为艺术”。不过, 在我仔细阅读他们的文本后, 却发现情境主义关于建构情境的具体理论分析几乎没有。比如具体解释situation是什么意思?situation要反映一种怎样的理论冲动和建构?都没有。他们倒是有些非常奇怪的概念, 如Psychogeography (心理图录) 、dérivé (漂移) 和Détournement (异轨) 等。这个“异轨”, 就像火车道的扳道夫, 让一辆火车异轨, 变到另外一根轨道上去, 这跟后来晚期海德格尔的“跳出”概念是一样的, 这个意思是说不再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走, 我不跟你们玩了, 我换一种话语, 完全跳出这条道路。这些方式, 实际上都是艺术家的创造过程:在艺术领域, 包括布莱希特那个“陌生化”的戏剧, 即通过一个戏剧化的夸张效果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熟悉的东西重新陌生化;在超现实主义那里, 就是对肯定性建构现实过程的一种反叛。例如在小说写作过程中采取一系列诸如意识流等跟生活完全不一样的“白描法”, 包括自然主义的一些描写。他们所做事情的就是, 正常人习惯的思维是一个线性流淌的过程, 正常生活的一段段的逻辑链接, 而他们的努力则会造成所有东西的中断, 然后以这种超过现实生活的熟悉 (麻木) 的东西的状况提供一个新的革命性的状况。这就叫“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这种先锋艺术就是对建构性的现实的一种批评, 所以情境主义和之前的超现实主义都是反建构论的。
其实, 建构论有两个含义, 它表层的含义是肯定和支持一种现实过程, 比如传统的知识积累建构论是肯定性的建构主义。反建构主义者, 像拉康、超现实主义, 他们是把我们习以为常地建构起来的现实消解和打碎, 实际上, 这也是更早的一种解构论。建构论的第二个层面, 跟我前面的讨论有关联, 所谓建构论的问题是反实体主义的, 就是我们所有理解为肉身的人的部分, 被消解为建构性的关系存在, 像皮亚杰就是建构论的, 他的发生认识论非常复杂。广松涉也是建构论和关系本体论。在社会学里也有社会建构论, 历史学里也有历史建构论。建构论的第二个层面慢慢形成一种新的趋向, 以功能性的建构取代实体中心论, 它是关系主义系统论的。所以, 在后面这一点上, 情境主义反而与新建构主义都有很多相似点。
可是, 我自己的所谓构境论说到底并不是来源于此。在从实践结构的思考走向当代思想史的进程中, 不知道哪一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即中国的思想家将来要提供一种自己的思想, 绝不可能以他人的名义言说, 我们不可能用西方学者的话语表达自己的学术存在, 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学术身份认同, 中国人必须要以东方的学术话语来言说。过去, 我从黑格尔、马克思开始, 然后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说来说去, 实际上我们都是在用西方的话语来进行言说, 如果真正要提供一种与世界学术对话的中国当代哲学思想, 那它必然是以我们自己民族的学术话语方式出现的东西。当然, 我并不是现在就打算进入孔孟、老子和庄子的东西, 但以后是一定会做的, 因为总要回到我们民族文化中根基的部分, 可是, 我觉得并不需要现在花很大精力去做, 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要进去太容易了, 我们的生命和存在就和那部分东西相关。现在需要在“外面”, 用他性话语来做一个世界性的游历, 然后再回来重构传统中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 构境论的“境”是我对东方体知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重构。依我之见, “境”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范式性的概念。王树人老师曾经用了一个词是“象文化”, 但我认为象文化没有表征出我们民族文化最核心的部分。“象”一定是和“看”相关的, 象、图像、景象, 甚至意象必是与视觉相关的可视的表象。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 不管从它的实践理性层面、理论的学术层面, 还是从它的所有的文化艺术存在层面, 甚至到生活关系, 然后到官场的权术, 却都不是可言谈的场境。所以, 佛学到了中国一定是禅宗, 禅宗的核心一定是“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什么东西到了中国, 所有表象性的, 外部可见的东西都被扬弃掉了。它变成一种体知的情境性的东西, 就像我们懂一点中国的绘画或书法的人都会知道, 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都是对图像和可见的书写之形的超越。我说过, 从近代的梁启超到当代草圣林散之的东西, 从一般人的直观来看就像小孩三四年级写的东西。包括江苏一位书法大师萧娴先生的字, 视象中的在场总是歪歪斜斜地刻在纸上, 实际上, 读这些大师的书法作品时, 他们的功法都不在直观中的象, 而是一种很深的由作者与观者共同建构起来的意境。在我看来, 东方文化是情景化的、意境化和诗境化的。我们中国人学术上根基性的东西和所有西方的物性话语相比, 其根本的差异性就在这里。西方文化只是在当代发展中, 物极折返中才开始向构境论回归, 如拉康和海德格尔的晚年思考。我常常在想, 中华民族的文化存在的确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最高点, 但这种依存于传统农耕生存的“最高点”不过是黑格尔所讲的一个抽象的原点, 它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复杂的不同文化的铺垫、填充才能走到具体的抽象, 以生成当代文化中真正的最高点。我当时脑子里一转弯, 提出构境论, 实际上假设的是一个中国哲学家以中国文化最根基的一个支点来表达一种新的东方文化或者思考的走向。但怎么走到这一点的, 我还没有想得很清楚。
问:您刚才把“构境”的“境”做了说明, 能否把“构”的涵义再略微展开一下?
张:准确地说, “构”不是实存的。构境论中“构”不是一个可以被分开讨论的独立实存, 或者说可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对象。就像Sein一样, 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 它恰恰是不能对象化摆置的。“构境”中的构, 实际上就是成境时的那个突现场境发生。应该承认, 我的构境论是与突现论相关的。1992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1) , 明确提出意识的本质是一种操作性建构关联现象的突现, 也就是大脑皮层中那个神经突状体系统互动的交合过程和物理过程所产生的一个特定现象。意识是一个突现构境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虽然它始终与大脑的物理过程有一个物性连接, 但它已经不是物理现象。所有意识都是一个突现过程, 我们去感受的时候, 是大脑里面发生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电流所建构的场境突现存在。前段时间, 法国著名哲学家马拉布 (Catherine Malabou) 访问南京大学。她的那个可塑性学说就与大脑皮层活动的脑科学直接相关了。
建构, 或者创造一种结构, 实际上是form这个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从古代往后走, 慢慢就产生了“赋予一个形式”、“给予一个结构”一类的塑形 (formation) 或者构式 (configuration) 这样的概念。梁康在译胡塞尔的过程中, 也将德语中Ausformung译成赋形, 就是给予一个形式, 观念的赋形。但我们讲概念赋形, 不是说我们在一个感性过程里, 我们动手去把它做成一个东西, 不是。它是指一个观念被无意识地结构化的过程。胡塞尔说, 我们要从前见那个根本不自觉的, 所有传统的赋形当中摆脱出来, 把它加上括号搁置起来, 由此返回到真正的形式显现的观念直观中, 显然, 现象学的还原也是一个方法论自觉的过程。仔细去想, 它在讲赋形的时候, 就是把不自觉的给予方式重新自觉地指认出来。通常, 胡塞尔一个学期只讲一件事情, 比如我怎么看到我手上的这个杯子?他会把杯子呈现中的感知的形成过程, 还原为一个赋形和被简化成建构的过程。其实, 不同层次的塑形过程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外部的shaping, 在艺术雕塑中, 一块泥巴或石头, 雕塑家给予它一个外部可见的新的艺术存在形态;再比如海德格尔带着伽达默尔做木工活, 都可以用这个shaping。然而, 马克思在德文里用这个塑形 (Formung) 概念的时候却很不一样, 劳动塑形和一般的可见的外部塑形是不一样的, 他所指认的劳动塑形非常复杂, 在工艺学的视角中, 劳动确实发生了一种从外部改变一个事物的物性形式 (使用价值) 的过程, 但是从商品生产的历史性视角上看, 这个劳动塑形同时也给予自然物一种全新的社会存在 (价值) 。这是一个双层构式的过程。
似乎, 海德格尔把这个塑形过程更加复杂化了。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文章 (2) 中, 主要讨论了海德格尔的“意蕴世界”这个概念, 在那里, 塑形本身不仅给予了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 它同时还建构出面向特定主体的一种意蕴情境———世界。它使这个物性塑形与主体始终发生一个连带关联与境, 这里海德格尔用了一个词, “遭遇”。海德格尔举例说, 他在他的阁楼上遇到了年轻时候用过的那块破损的滑雪板。滑雪板是当年工人劳动塑形的物性结果, 可是, 他说自己遭遇的不是一个被曾经塑形的滑雪板, 而是遭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他这里的塑形概念, 变成了一个主体本身存在情境与原来那个物性塑形物被上手使用的特定关系, 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情境重构, 非常复杂吧。当你在问构境论的“构”是什么的时候, 它会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怎样构境的思考域。海德格尔是从现象学的形式显示的观念赋形开始思考的, 他专门有一个演讲就讲这个问题。他发现, 胡塞尔的很多重要的现象学判断是局限于意识领域, 于是, 他就努力把它延伸到人的存在和生命过程当中, 如果说生活世界在胡塞尔那里是一个概念, 那么在海德格尔这里则是他全部存在论的基础。
1922年, 青年海德格尔在《那托普报告》中最初建构存在论的基础时是非常复杂的, 他用很多概念替代了原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概念, 比如用关涉 (Sorge) 替代了马克思的“实践”的概念。因为实践是个社会层面的宏大叙事,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劳动塑形概念, 讲的也是对外部物质对象的改造, 海德格尔没有去考虑这样一些宏大问题, Sorge是有死者此在去在的方式。熊伟先生把Sorge这个概念翻成中文的“烦”, 也有道理, 但我没有赞同这个译法。Sogen这个词是德文中最平常的词, 也就是英文的care, 关心, 当把它翻成“烦”的时候, 构境理解中就会意会成一个主观性的东西———烦、不耐烦。庆节他们后来翻译成“操心”, 或者烦心、烦神, 都容易引导到主观构境的情境中, 至少带有一点主观的意味性在里面。海德格尔的Sorge构境层中的确存在主观成分, 但他的真实构境意向是走向客观现实和物性的操持, Sorge这个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做什么”, 关涉是此在带有他的意图, 带着他的情感走向外部的过程, 总是指向一个关系性的对象化的东西。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 过去讲劳动, 马克思那里通常是不讲主观意图的, 但海德格尔的Sorge从起点上就有来自此在的关心, 所以, 我在《回到海德格尔》里面把它翻成“关涉”。“关”就是我主观意图中关注、关心的“何所向”, “涉”就是干涉, 干涉就是马克思用宏观实践来代替的客观作用的部分。海德格尔的思考起点———此在, 其实是在一定时间中的有死者———生存个体, 所以他的思考会非常的具体和微观。回到刚才我们讨论的构型和赋形, 它们的起点不是抽象的, 而是跟具体个人主体相关的, 有意图的进入。情境论的东西, 在海德格尔这里非常强烈, 也很复杂, 在他那里, 从赋形再深化到突现场境中的格式塔 (Gestalt) 。
Gestalt不是发生在一个与人没关系的过程中。海德格尔提及的所有的Gestalt, 它的情境、意蕴世界的格式塔很复杂, 它通常不是一个故意的建构, 它经常是突然发生的, 而且是在主体的意图之外的。在格式塔心理学里面, 格式塔场境的突现是瞬间的。经常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 一个人骑马穿过一片雪地来到山边的一个小旅店, 旅店店主吃惊地告诉骑马人, 说那是昨天刚上冻的一个深水湖, 讲完这句话, 骑马人当场就晕倒了。晕倒这个事件, 表明他心理感觉场中发生的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变化, 他突然想到刚才骑马过雪地的每一个瞬间都可能掉湖里淹死, 在他骑马过程中, 他的感知场是一片坚实的土地, 而他晕倒的一瞬间就是突然发生了一个断裂, 这个实地场境发生断裂, 而他随时坠湖身亡的格式塔场境突现出来。我们能看到, 格式塔这个所谓建构不是主观意图去做的, 他是一个断裂性的场境突变。海德格尔思想构境中讲的很多塑形、意蕴过程都是与此相关。
问:“塑形”这个词我不是特别熟悉它的理论涵义, 但是从字面上来说, 塑形好像就是又变成可视的、可言说的?
张:恰恰相反。塑形、构式和格式塔都是不可直观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他较早提出形式和质料的关系, 我们会把形式比较多地看作是给予质料的外部形式, 长、宽、高, 以及造型中可见的量化的形式。我现在还没有进行考证, 形式概念的改变、形式的内化, 或者形式的范式化和存在论化, 是不是应该从文学里面的那个形式主义开始, 从俄国的形式主义开始。因为, 雅各布森和索绪尔在语言学中讨论形式的概念的时候, 它已经不是语言的外部形式了, 他们已经开始描述作品内部的形式和语言内部的系统结构, 这些东西显然都不是可以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说, 结构主义会去思考, 小说和戏剧到底是作者主观意图的实现, 还是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受制于某种看不见的语言结构、文学符码系统统摄的结果?这个内部形式或理论结构恰恰是不可见的, 而正是这种不可见的结构决定了可见的人的主体和写出来的文字。形式这个内化过程至少在近现代是从文学评论形式主义这条线往后走, 到法国的语言学结构主义, 这是一段。另外, 形式在西方哲学史上可能发生过多重变化。估计到了近代以后就不一定指那个外部的形式了, 这个我没有具体考察过。
问:我想问的是, 您觉得传统文化中那个“境”要比王树人老师那个“象”更为重要, 因为象是可视的、可言说的, 那“境”我们如何去把握、去体会?或者说应该用一个什么动词?然后赋形的过程是否就是对情境的一个把握的过程?
张:“体知”境。在赋形的过程中还谈不到构境的过程, 塑形、构式和构序都只是构境的前期物性场境存在, 境是最后在人的最高存在层面出现的突现状况, 以及精神层面和艺术感知层面构境, 构境不过是人的存在层面的一个最高点。回到书法的这个例子。书法的开端同样是从形开始, 从一笔一画临摹, 只是到了最高的境界上, 才达到情境论的顶点上, 进入超越外形的意境体知过程。学书法的过程, 开始可能几年、十几年是在形构的过程当中, 它是外部的, 慢慢才能深化到内部的对这整个书法结构奥秘的内在形式的理解, 这是不一样的。从外部的形到内部的境有个过程。
再回到刚才我没有说完的部分, 以海德格尔为例, 他从现象学形式显示中的这个观念赋形论开始, 恰恰是从形式显示的概念开始的。胡塞尔在现象学中集中讨论过观念的形式是如何被显现出来的, 然后海德格尔从这儿一点点往后走, 慢慢开始发现这个观念赋形的现实基础是与我们关涉活动建构起来的周围世界的塑形 (制作) 相关, 其中, 海德格尔还引进了一个重要思考构境线索, 就是有序性 (Ordnung, 即英文里那个order) , 在中文里面孙周兴老师把它翻出来了, 但我是用Ordnung这个词来表征构序这个概念, 就是关涉活动中给予相关事物存在的一个组织化的有序性, 为此, 海德格尔同时发明了几个概念, 去构序 (Zuordnung) 、入序 (Einordnung) 、等级排序 (Stufenordnung) 等。观念或逻辑入序就是使一个概念进入一个逻辑结构中的次序, 入序使赋形概念更进了一步, 如果说赋形是从外部给予概念一种显示形式, 这在使用概念进行言说和写作时是可见的, 而让你进入一种逻辑次序的时候, 它却是不可直接去把握的。没有办法直接去捕捉到构序, 只能通过一个概念在某一种思想系统中的具体功能位置 (用复杂性科学的术语来描述, 叫系统质) 去描述它。而我用的概念, 则是从劳动塑形到生产关系构式, 再到生产构序, 这与海德格尔《那托普报告》中的工作是平行的思考。在这一思路上, 佐恩·雷特尔 (Alfred Sohn-Rethel) 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 (1) 一书是极为重要的文本。在我看来, 他是第一个真正解决康德问题的哲学家。
从这里, 我们再回到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塑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劳动塑形是一个双层塑形, 而马克思强调的恰恰是一种不可见的生产关系构境层, 相比之使用价值意义上的实物存在方式的可见造型, 价值形态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形式是不可见的。其实, 整个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都是不可见的。并且, 人与自然的物性塑形关系背后就是构序性的生产力概念, 它指示人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水平, 最后, 在整体上马克思指认了社会存在本身的本质, 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特定历史结合中发生的一种不可直观的关系结构, 他给了一个更大的概念, 就是生产方式 (Produktionsweise) , 在这个概念里边, 他没有用“形式”, 而是用weise (即英文中的model) 。生产方式这个概念, 它更是不可直接在直观中达到的东西。对生产方式, 我已经用了“筑模” (modeling) 这个概念来重构它, 以表示生产方式是在不同力量关系较量的动态格局中生成的。生产方式随时在发生, 在流动, 恰恰是在这个发生和流动的过程中, 金融结构、市场交换方式、劳动的国际化分工, 马克思讲的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 内部形成一个特定的资本构成模型, 一个功能性的模型, 即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筑模。
作为生产方式的筑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下的建构与解构。建构与解构随着活动的发生和停止而在场和消失。正如我上课经常跟学生公开说的一个玩笑:社会生活晚上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社会存在总是一个当下发生的建构过程, 它是一个在多层次上, 从劳动塑形到社会筑模同时发生的非常复杂的过程。为什么晚上不存在?所有人都睡去的时候, 人和人建立的所有的关系性的活动和力量关系都不复存在, 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社会生活是没有的, 就像我们经常在美国恐怖片里看到的, 一个城市所有活动都停滞了, 所有的物性东西都在, 但是当所有人都不活动的时候, 社会并不在。因为, 所谓社会存在是第二天早上所有人通过上班、劳作和学习, 通过活动重新在力量关系中建构起来的, 所有的劳动塑形到生产构式到社会筑模都是当下发生的。一个所有人停滞的瞬间, 存在即被解构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区别于全部形而上学的存在者论, 存在和存在者的差别就在这儿, 而传统旧哲学把当下发生着的关涉性的存在变成了物性实存着的对象性的东西。在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意义上, 社会生活晚上都是不存在的。这是我的构境论在社会场境论层面上的一个奇谈怪论。
再极端一些讲, 在夜间, 整个“社会”也是不存在的, 因为, 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 (Gesellschaft) 恰恰是由市场中介关系所建构的。应该特别说明一下, 马克思关于社会的观点其实是历史性的。依马克思分析, 在经济社会形态之前, 是不存在“社会”的。那时候, 马克思把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们的共同群族生活称为共同体 (Gemeinschaft) 。精准地说, 封建制度也应该是人对人依赖关系建构起来的共同体, 那个建构封建等级的血亲宗法关系 (我是我妈妈的儿子、查尔斯王子是贵族) 在晚上仍然是实在的, 封建制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我认为, 当马克思使用社会概念的时候, 是跟着黑格尔往下做的, 社会这个概念就是人不再是通过血缘关系直接相关, 而是通过市场交换建构起来的一个非常奇怪的自发建构起来的中介系统。就像《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那样, 在新型的资产阶级世界中, 人跟人的脉脉含情的亲情关系全消失了, 突现的是市场中介化了的金钱关系场境, 这才是现代社会的筑模。在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本身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之后才出现的, 社会一定是通过中介性的关系重新建构起来的。不是说, 我们自觉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而是在每个人追逐自己私利的时候, 社会当下被构式与发生。从商品生产的劳动塑形到资本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关系构式再到整个社会生活的筑模, 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是在人基于工业现代性活动中发生的, 相对于个体, 绝大部分生产方式或者筑模决定我们的生活, 但恰恰又是我们所有个人的活动才使它发生和存在。这是后期萨特思考了但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就像我们建构了商品世界, 然后货币—资本系统重颠倒了过来支配我们, 这就是马克思的事物化和拜物教批判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如果它是一种建构论, 这个建构论和一般所理解的建构论根本不是一回事,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从存在论进入, 与对社会存在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 以及对所有的社会生活的理解相关, 构境论只是在场存在基础之上更重要的一个上层部分。
在上一次我回答周嘉昕访谈提问 (1) 的时候讲过, 构境论只是我对生活理解的一个顶端部分, 这个顶端部分会跟精神生活更近一些, 比如文本解释情境。但是, 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 一个人活着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情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构境论是一个非常具象的过程, 因人而异, 比如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到海德格尔贵族哲学的那个理解的思境。生命存在也是如此, 每一个人的生存情境都是不一样的, 会出现无数不同层面的存在场境与精神构境。我想讲的问题是, 人追求他可以达到的那个快乐的生命之境就行了。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 我在拉康哲学中获得的东西是:绝大部分人生活在一个伪相当中, 那是一个他性的幻境。在这个意义上, 拉康实际上是写了一部西方的《红楼梦》。在其中, 人们追逐物质世界, 生命的所有意义在于追逐这样一些由他者欲望建构起来的物质利益, 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 我们甚至还没有提升到近代启蒙思想以来对物化的批判境界, 甚至还不如中世纪神性提升的那个人的存在。当然, 所有关于这个构境论批判的过程都是关于隐性事物的思考, 有如巴什拉所讲的, 它不是可见的。我从去年开始讨论福柯—阿甘本哲学中可见与不可见的关系, 在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已经讲过, 今年会再到中山大学讲“看到不在场之物———阿甘本思想”。你们会看到, 现在真有很多大师跟我一起思考同样一个问题, 进入与大师对话的过程, 有可能接近构境论的思考。
至于你提到情境的“重演”和“发生”, 这是海德格尔的历史观点。“发生”就是后来他用的“本有”那个概念, 就是Ereignis。“重演”概念跟我很接近, 我经常会用“重构”这个概念, 我会讲重建一个历史生活的场境。重演是对原来发生的那个社会场境的复现, 我这里面是在历史研究中重新构境的过程, 重构与当时发生的那个情境永远不会是完全重叠的。所以我会在《历史研究》上写历史构境论那篇文章。 (2) 原因在于, 直到今天我们的史学还坚守着如下这样观念:一种历史研究过程是我们面对历史事实, 真实地客观地还原历史的过程, 却不知这完全是个假相。第一, 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历史事实本身是被建构的;第二, 我们面对这个建构的历史事实的复构过程, 永远不可能和真实发生的生活重叠。并且, 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不入史的, 特别是跟个人生活相关的场境。历史本身的重构和重演是打很大折扣的, 是不可能还原的, 不可能真正客观主义地写实。福柯后来的考古学和谱系学历史研究, 都在力图解决这个问题。
问:引入新概念是您论述中挺突出的一个特点, 这多少让人觉得您的构境论“界面”不够友好。面对这些新概念, 人们会有种无话可说、无言以对的感觉。以您的“社会结构筑模”概念为例, 它是对生产方式概念的“现代重写”, 但我个人觉得, 字面上完全抛开了“生产方式”四个字, 在注入现代内涵的同时, 是否会牺牲掉为对话提供平台的诸多思想资源和理论线索?而且思想史上许多重要概念, 虽然增加了相当多的时代内容, 但坚持“旧瓶新酒”的现象并不罕见。您如何看待引入新概念在理论建构方面造成的得失?您在《构境论到底想说明什么?》 (1) 一文中曾解释过为什么不顾大家的质疑、批评甚至些许反感, 会很果断地引入一些新概念。这里能否再请您多讲几句。
张:在思想史上, 大师们的做法都是不同的, 它会呈现多个构境层。第一, 内涵置换法。在整个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 有一些概念是没有办法革新的, 像海德格尔用的存在概念, 始于古希腊爱利亚学派, 中国传统哲学里面也有, 大师们的做法常常是彻底置换这一原有概念的内涵, 以实现思想革命, 我们在海德格尔存在概念里找不到形而上学的影子, 传统的存在概念被宣判为对象化、石化的存在者。第二, 概念替代。比如人这个概念, 海德格尔从克尔凯郭尔已经超出类的个人进一步走向一定时间中的有死者———此在。而在拉康那里, 人不再叫做人, 而是叫做“症候构成物”。其实, 拉康的做法已经是创造新概念了, 这是第三种做法。
创造新概念, 是一个思想家认为传统研究中的某一概念已经无法再通过置换法和替代法实现自己的用意时, 必须选择启用新的有具体异质性内容的全新概念。比如, 塑形概念并不是我的发明, 我至多是重新标注和挪用, 在西方思想史上, 它是对形式概念的深化, 从form到德语中的Ausformung或法语中的formation, 它并非仅仅是今天构词法中的变化, 而是体现了人们在对事物和现象存在形式方面认识的深化:从质料与形式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深入到正在言说和布展着的话语塑形研究, 已经不仅仅是从外部到内部, 而且意味着思考方式本身的变革。新概念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概念本身, 按阿甘本的说法就是, 福柯的相当多的新概念对他而言都是一种范式, 范式就是说新概念的引入本身就是新方法或方法论变革。范式论是从库恩那里开始的, 一种重要的科学理论结构决定了所有科学实验和理论归纳的生产过程, 它的变革通常是通过断裂性的革命得以发生。
所以, 创造性地引入一些新概念或者概念自身的重构并不是概念的简单替换问题, 往往这种概念性革命的产生会导致整个思想史的重写。比如说, 存在概念从爱利亚学派到海德格尔的重解, 本体论从古代基始本原论直到存在论的内涵变化, 发生改变的并不是一两个概念, 而是重写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这种状况, 我们在黑格尔那里也曾经看到过。实际上, 有多少大师就会有多少种重写的思想史, 在这种重写中, 一方面, 思想上的原有概念发生重要的重新诠释, 另一方面, 出现代表思想革命的新概念。新概念实际上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新范式, 比如说现象学这个概念, 在康德和黑格尔的意义上, 它代表了一种现象与本质之间的批判张力, 而到胡塞尔, 则在塑形自身的还原上导引了近代欧洲思想最重要的变化, 你说现象学是一个概念,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概念, 而是一种革命。刚才讲到“筑模”概念, 是皮格林使用modeling一词, 它呈现了正在发生建构中的方式, 筑模就是表示这个模型是在不断地变化当中, 在功能性发生当中建构起来的一个东西。这个词显然直译不过来。筑模这个词, 如果回到马克思原初的德文语境中的Produktionsweise, 也是应该在动词意义上去理解的。原来, 我们把生产方式变成一种现成的存在者意义上的概念, 引入modeling这个词, 再回到马克思原来的语境当中, 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根本性的理解视角的变化。
海德格尔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中也比较关注对新词的引入, 并且在他认为传统的德文无法表述自己全新的构境时, 他还通过使用古高地旧用德语或用短线分隔法造词, 好在我还没有造词, 中文字造不出来。海德格尔为什么会造词?在他秘密写下的本有论哲学构境中, 他认为正在使用中的整套德文的语言系统都和存在论相关, 都是沾染了存在论的暴力征服性的特征。所以, 他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言说方式, 在他的《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 (1) 一书中, 几乎对所有概念都进行了重新构境, 对于存在论中的Sein, 他重新启用了古高地德语当中的词, 比如将Sein中的i变成y, 重构出Seyn的全新构境意义, 使原来那个词形式上发生变化, 读音一样, 但意思完全不一样, 成为一个同音异义的新字, 生成在走向本有过程中的存有概念 (德里达在“延异”这个概念的构境式制作中, 也沿袭了海德格尔的这一做法) 。然后, 此在从Dasein中加短线“-”, 成为Da-sein, 加有“-”的此在跟原来去在世的此在就不一样了, 他将是弃绝存在的牧羊人。当概念本身没有办法变化时, 海德格尔就采用这个方式来重构原词的新境。
其实在我看来, 不接受新的概念, 恰恰证明人们无法放弃旧有的思维模式。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中, 概念和方法论创新的过程是比较自觉和迅速的, 思想家比较习惯于汲取自然科学、艺术或其他方面涌现出来的新的概念、新的理解的方式, 很迅速地消化和引入到自己的研究当中, 这已经成了一个惯例。但是, 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偏向保守的, 加之前苏东的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的灌输, 研究者习惯于用永恒不变的原有概念和学统。举个例子, 西方文本学研究中出现的“语境”这个概念, 讲的是文本分析里面作品的上下文关系, 有特定的意思, 当我们去读一段文字时, 这一话语片断的意义, 不可能在这一文字直白里直接表达出来, 它只能在这一话语片断与上下文话语塑形关系中才能得到反指, 甚至, 还会涉及文本和文本之间、文本和社会关系、文本与其他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通常我们一讲语境, 指上下文, 其实, 作为一个新概念和新范式, 它是在表达一种特定复杂关系的情境。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使用这个概念, 比如“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有些老先生就很反感, 当时在一个会议上, 我的一位老师就讲了一句话:“我以为是什么新东西呢?你很喜欢用新概念, 我最后弄清楚了, 语境不就是背景吗?你非要把‘背景’这个概念说到我们不懂。”你看, 背景是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还用, 但在背景中再更深地去强调一个非常特定的关系构成的指向焦点的这样一个语境, 它却是不一样的。当然, 现在“语境”这个概念大家慢慢都能接受了。包括建构、解构、话语等概念, 现在连公众舆论里都有这样的概念了, 我觉得我们这些先吃螃蟹的人会有很大功劳。
问:这里扯开来讲一下, 您说引入新概念, 那西学东渐、五四白话文运动啊, 引入了多少新概念。您说那代前辈批评您用新概念, 我还是有点不理解。
张:这是一个重要的思考节点。五四运动时, 包括像鲁迅、胡适那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从文言字到白话文的推进造成了话语描述方式的剧烈变化。他们正是要脱离传统话语表述方式, 那时非常自然地从西方拿来大量的新概念, 所以早先的拿来主义在新文化运动里是非常正常的, 白话文和新体诗中有大量翻译过来的新东西, 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可是, 在我的老师这一辈人中, 他们受过传统文化教育, 也经过革命的锻炼, 但他们真正接受的哲学训练却是前苏东教科书体系的强制性思想塑形。斯大林教条主义体系同样是强加给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个外部概念体系, 虽然这一概念体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进来的时候, 对中国人来讲全部是新概念, 但长久以来它异化成了一种强迫我们接受的固定的苏式理论话语。说它是苏式话语, 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都是从德文译成俄文, 再从苏联专家编译话语塑形之后译成中文的。所以, 虽然我的老师们也有很好的国学功底, 但几十年的政治塑形强制之下, 当他们思考哲学时, 只能使用苏式话语, 这成为一种隐性的惯性话语。他们习惯了用那个理论框架来进行思考, 特别是在关于马克思的理解上, 如果在表述方式和理解上存在与那个传统解释框架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就会接受不了。
不说贡献, 用当代中国学者自己的方式或另外一种话语来描述马克思, 这本身就是对一种苏式话语禁区的突破。而且, 如果孩子气一些的话, 我就不用前苏东原来用过的概念, 你们原来所有使用的范式我都要把它解构掉。现在, 我觉得我们要从几十年人们强加给马克思文本的意识形态话语里面摆脱出来, 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这还不仅仅是对马克思, 对后来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一直到海德格尔, 到其他方面的东西。所以, 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也会在我的《回到海德格尔》这本书里面见不到他们熟悉的海德格尔, 然后, 接下来依西方哲学来读福柯的人会在《回到福柯》中见不到他们所熟悉的福柯, 我觉得这是件比较好的事, 不是件坏事。我的老师孙伯鍨先生在批评我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人家一辈子不会有一两个新概念, 你一天一堆新概念!但孙老师也没有真的打算制止我。我如果不这样做, 就没有张一兵了。
注释
1张一兵:《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 (第一卷)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2张一兵:《关联与境:狄尔泰的历史哲学》, 载《历史研究》, 2011年第4期。
3情境认知理论 (Situated Cognition) 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让·莱夫 (Jean Lave) 教授和独立研究者爱丁纳·温格 (Etienne Wenger) 于1990年前后提出的一种新型的教育理论, 主张知与行是交互的, 知识传递是情境化的, 教与学是通过情境化活动不断向前推进。
4情境领导理论 (Situational Leadership) 是组织行为学家保罗·赫塞 (Paul Hersey) 和管理学家布兰查德 (Kenneth Blanchard) 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新型领导理论, 它着重从领导者、被领导者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研究领导效能的理论。
5情境语义学 (Situation Semantics, 简称SS) 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种新的语义理论, 创始人为美国逻辑学家巴维斯 (Jon Barwise) 和佩里 (John Perry) , 代表作是1983年出版的《情境与态度》 (Situations and Attitudes) 一书。它主张, 现实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情境构成的, 某时某地某个体 (或某些个体) 具有某性质 (或某关系) 这样的事实就构成一个情境。情境的构成要素有:个体 (individuals) , 用a1, …, an表示;关系 (relations) , 用r表示 (一元关系又叫性质) ;时空单位 (space-timelocations) , 用l, l′…表示;真值 (truth values) , 用i表示。一般来说, 情境通常表现为若干事件的过程 (course of events) , 用e表示。事件 (event) 是由时空单位l, 个体与关系组成的序列y=〈r, a1, …an〉, 与真值i∈{0, 1}构成的序列〈l, y, i〉, 情境e就是若干这样的序列组成的集合。
6德波:《景观社会》, 王昭风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范内格姆:《日常生活革命》,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版;德·赛托:《日常生活实践》 (第一卷) , 方琳琳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这些先锋团体主要有:实验艺术家国际 (The International of Experimental Artist, 简称COBRA) 、字母主义运动和字母主义国际 (Letterist Movement[简称LM]and Letterist International[简称LI]) 和包豪斯印象运动国际 (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an Imaginist Bahaus, 简称IMIB) 。这些团体的形成, 大都与欧洲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关, 尤其与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社会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悲观情绪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禀承了达达主义、未来派和超现实主义的传统, 或者本身就是那样的派别, 试图以各种先锋派艺术的方式反抗或改造异化的西方社会现实。
9张一兵:《论意识空间的操作本质》, 载《哲学动态》, 1992年第3期。
10张一兵:《意蕴:遭遇世界中的上手与在手》, 载《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期。
11雷特尔:《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 (Geistige und k觟rperliche Arbeit:zur Epistemologie der abendl ndischen Geschichte) , 此书已经由谢永康博士等译成中文, 正在审订, 不久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2张一兵、周嘉昕:《承认相对和有限的客观性》, 载《理论探讨》, 2013年第3期。
13张一兵:《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构境》, 载《历史研究》, 2008年第1期。
14张一兵:《构境论到底想说明什么?》, 载《学术月刊》, 2009年第7期。
15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文章来源:《哲学分析》2014年 第3期。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

 上一篇
上一篇